|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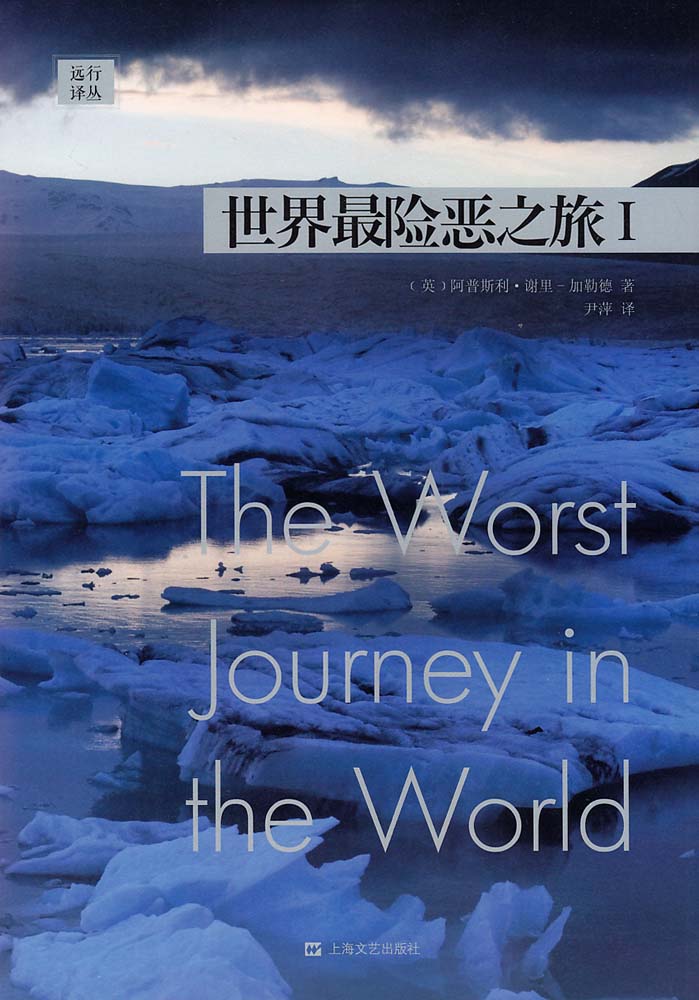 极地探险是最清洁也最孤独的受苦方法。只有在极地探险时,你可以一件衣服从九月穿到十二月,除了一层身体自然分泌的油脂外,衣服看起来干净如新。在极地比在伦敦更寂寞,比在任何修道院更与世隔绝,邮件一年才来一次。常有人争论,是战时的法国艰苦,还是在巴勒斯坦或美索不达米亚难熬;而其实,跟在南极的日子相比,这些都不算差。坎贝尔那组人里有一位就告诉我,在比利时打仗蹲壕沟,与南极的日子相比,算是相当轻松愉快的。但是当然,除非有人发明什么艰苦量表,否则很难比较。总的来说,我不信世上有谁的日子比帝企鹅更苦。 极地探险是最清洁也最孤独的受苦方法。只有在极地探险时,你可以一件衣服从九月穿到十二月,除了一层身体自然分泌的油脂外,衣服看起来干净如新。在极地比在伦敦更寂寞,比在任何修道院更与世隔绝,邮件一年才来一次。常有人争论,是战时的法国艰苦,还是在巴勒斯坦或美索不达米亚难熬;而其实,跟在南极的日子相比,这些都不算差。坎贝尔那组人里有一位就告诉我,在比利时打仗蹲壕沟,与南极的日子相比,算是相当轻松愉快的。但是当然,除非有人发明什么艰苦量表,否则很难比较。总的来说,我不信世上有谁的日子比帝企鹅更苦。
一直到现在,一般人眼中的南极,仍然像古巴比伦人心目中的众神居所一样,是一片高耸的大地,在辽阔大海的彼端,环绕着凡人的世界。光想想有这么个地方已经够骇人,更别提要去探索。因为,公元九世纪,阿尔弗雷德国王统治英国时,维京人已经在踏勘北方冰原;可是直到一八一五年威灵顿将军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时,南极大陆还未发现。
如果想要读南极探险史,斯科特所著《发现号之旅》(Voyageof the Discovery)中有一章写得极好,别的一些书上也有。本书并不做此图。不过,有人向我抱怨,说《斯科特的最后探险》(Scott's LastExpedition)一书交代不清,好像以为读者对一切都熟得很,而其实读者完全不清楚“发现号”是个什么,城堡岩(Castlle Rock)或小屋岬(Hut Point)又在哪里。为了让读者了解本书中所提历次南极探险的重大发现和遗留的痕迹,我在此做个简短的介绍。
库克:奠定南方大地的知识基础
打从一开始,有人绘制南半球地图时,就认为那里有一块大陆,命名为“南方之地”(Terra Australis)。探险家越过好望角和合恩角之后,却只看到汹涌的大洋,不见其他。后来又发现了澳洲和新西兰,对南方大陆的信心减弱了,不过并未放弃。以前,探险是为了个人或国家事功;到十八世纪后半,追求科学新知的热忱为探险增添了动力。
库克、罗斯和斯科特都是南方大地的贵族。是英国大航海家库克奠下我们知识的基础。一七七二年,他指挥四百六十二吨的“果决号”和三百三十六吨的“冒险号”,从伦敦近郊港口德特福德启航。这是两艘运煤船。他和南森一样,相信食物成分多样可以防止坏血症。在记录中他提到,除了他的口粮“肉汤、胡萝卜泥和麦芽啤酒汁”以外,还打造了勋章,“送给新发现国家的土人,证明我们是最早的发现者”。不知道这些勋章现在还有没有留存。
抵达好望角后,库克向东南下到新西兰,打算尽力南航,寻找那南方大陆。一七七二年十二月十日,在南纬五十度四十分,东经二度处,他第一次看见“冰岛”般的大冰山。次日,他“看见一些体型如鸽……挑选装备和人员是比较容易的,而要兼顾两个目的就要困难很多倍。斯科特和队员们都不愿只为探极这一个目的去,不过他们认为探极是值得尽力达成的目标。他们的态度是:“我们冒险,我们知道此行有风险,后来事情发展不利,我们没有理由抱怨……”
这样一种做事系统,我不敢说完美,但是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发展到相当精密的地步,一定得完整传授给后来之人。我讲述这个故事,希望以后的南极探险领袖能够拿起这本书来说:”根据这本书,我知道该订什么,订多少,给这么多人,在这么长的时间使用。我知道斯科特曾经怎么使用这些东西,他所定下的计划实行起来如何,他的队员在过程中做了哪些修改,对后人有些什么建议。我对其中哪些地方不是很同意,但这是一个基础,可以节省我很多个月的准备时间,对于探险的实际作业提供有用的知识。“如果这本书能让将来的探险者鉴往知来,就不算白费笔墨了。
不过,这不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一九一三年我开始写作时,是以叙事官身份替南极委员会写的,条件是让我放手去写。我最想做的是说明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是谁做的,谁的功劳,谁的责任,谁拉了最多雪橇,谁带领我们度过最后最苦的一年(那一年,有两支队伍失踪,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时间再拖下去,大家都要发疯了)。这些事都没有记录。我通常只是受别人领导,没有太多责任,而且常常吓得要死,很多情况我根本不清楚,我自己也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