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讲故事,如《一千零一夜》山鲁佐德与国王,如《看不见的城市》中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尼日利亚豪萨族的《非洲夜谈》中,做了宰相的鹦鹉(是真的鹦鹉,不是人名)给它的鹦鹉儿子讲故事,以此为启迪智力、传授知识的方式。在本书中负责讲述的是一个多年自杀未遂的机械人,因此它的故事不近“人”情,也可以谅解……
“创作源于生活”并不准确,创作的源头是人。本书故事的主题则是人的“深情”和“不妥协”。故事主角都难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他们各有病态与怪癖,各有深情,以及,各有各的不肯妥协。人们习见的情景,是把感情摊成薄薄一大片儿,每个地方的厚度都差不多,有些人甚至对自己的伴侣也不见得会多青睐一些。但也有极少的人,把所有心力用在微渺的一点上。指头戳不破布,但针尖可以。戳破了,那一边是不一样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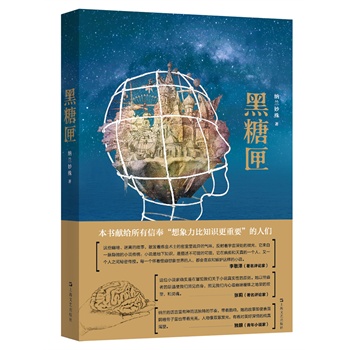
我对这些故事的质地的期望,是“轻盈”一点,就像The Beatles的歌《Nowhere Man》,“He's a real Nowhere Man,sitting in his Nowhere Land”。我希望它们不接地气,因此努力回避了真正的人名和地名(一切总是先被名字钉死的)。
这些故事在当下的文学氛围里显得格格不入,“文学氛围”就像个沙龙,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穿了一种风格的衣服,画面非常和谐。忽然进来了一个扮成疯帽匠(《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爱丽丝的好朋友)的人,站在身穿正装和晚礼服的先生女士之间,的确有点格格不入。不过幸好大家没赶他出去,他总算也可以坐下来喝杯樱桃酒,吃一块乳酪蛋糕,暗忖:其实请柬上没有规定着装嘛。
希区柯克有这么一段话:一个家庭主妇,每天下班回家的程序是做饭,吃饭,然后戴上橡胶手套洗碗。某天,丈夫说,亲爱的,今天不要洗碗了,戴上你最好的珍珠项链和戒指,我们到电影院去看场电影享受一下吧。于是这个主妇脱下橡胶手套,戴上项链和戒指,欢欢喜喜地跟着丈夫到了电影院。放映厅里黑了下来,主妇怀着激动的心情凝视银幕,她看到了什么呢?她看到一个家庭主妇,戴着橡胶手套在洗碗。
我猜有很多人(包括我)翻开时下很多小说时的心情,跟那个家庭主妇庶几相似。
当然,有人就喜欢看戴着橡胶手套洗碗的主妇的故事。不过,总会有些观众希望别的影厅上映点别的……
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美学体系,在自我教育的过程中,他会通过不断的筛选,有意识地咀嚼吞食特定的材料。英国有句谚语:You are what you eat。当然,偏食肯定不好,不过在东吃西吃的过程中,会慢慢清楚自己的口味。王世襄先生的公子谈烹饪,说,学做菜要从自己最喜欢的一道学起。平凡小人物的孤独寂寞,内心生活,人生世相,同一屋檐下心和心之间的千回百转、勾心斗角……这些我也很愿意写。不过在最开始这个阶段,我最迫切的欲望是先写点我偏爱的那种、奇特的故事,这期间借鉴的前贤有马塞尔·埃梅,阿拉斯代尔·格雷,安吉拉·卡特,阿里阿斯·卡内蒂,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再加上尼尔·盖曼,柴纳·米耶维,威廉·吉布森…… 尼尔·盖曼说:短篇小说是一场场前往宇宙尽头,却让你能及时赶回家吃晚饭的旅程……那些故事从没有真正离开你,如果一个故事打动了你,它就会与你同在,徘徊在你灵魂深处,某个你自己都难得一至的角落。 我真诚希望你会喜欢机械人里瑟先生在海边讲出的故事。 最后,感谢李敬泽老师,他的每次鼓励和褒扬,都令我迫切希望自己能写得再好一点。感谢我的先生小薛,他总是踊跃要做我的故事的第一个读者,并且每次都(不负责任地)说“比上一篇写得好”。感谢我的母亲吴存秋女士,我的父亲张江容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