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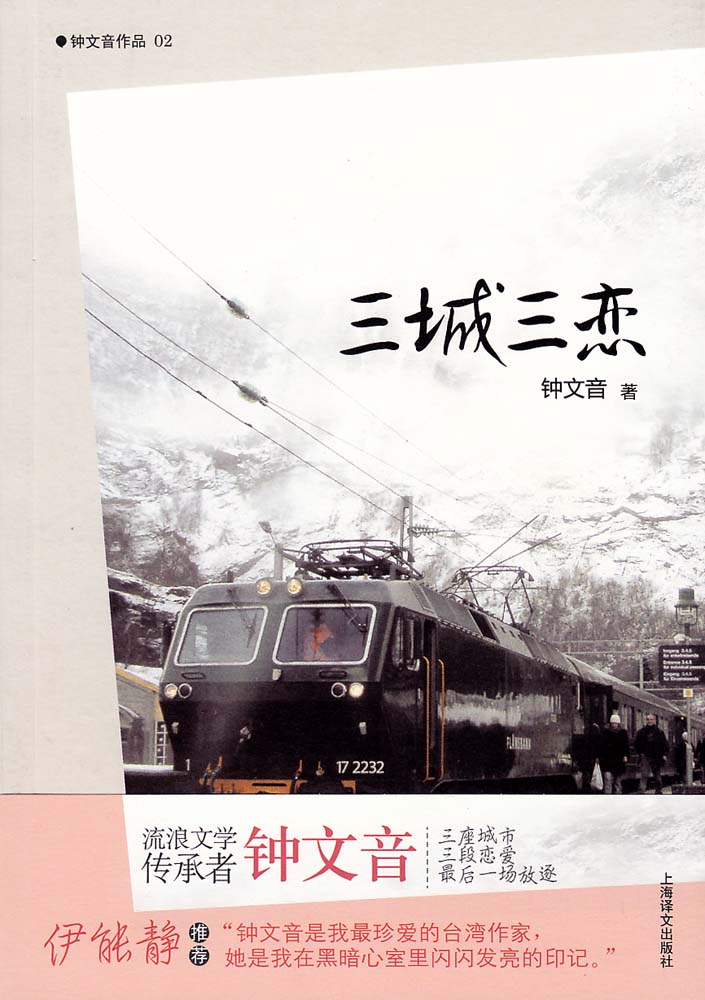 这是我生病最密集的一年,每天有新的病痛跑出来,不知道醒来疼痛将要转移至哪个部位。 这是我生病最密集的一年,每天有新的病痛跑出来,不知道醒来疼痛将要转移至哪个部位。
痛或可说是意志考验。
或许我呼唤他们太多了。
他们都具有悲剧的种子。
在旅途的笔记里,我写着想让芙烈达·卡萝和布拉格的卡夫卡交换命运。但写来失败,际遇不可得。
即使我假想卡萝真的和卡夫卡交换命运了,她可能不会重伤于车祸,却依然会遇上那要命的肺结核。
我知道卡萝躲不过命运。所以她仍然在墨西哥,我放弃将二者命运交换的书写。因为这样无用,为了找到一个独特的书写视角,却可能牺牲更多的现实探索。
就好比假设在现实人生里,我们交换成绩单,我们交换学历,我们交换情人,我们交换灵魂……如果命运转盘的落点可以选择,那么疼痛会不会少一点?然而如果生命依然是扭曲变形,你醒来是谁?你还有什么? 我还是我,卡夫卡仍是诚实的变形者,卡萝仍是骄傲的伤残者。而我想我们都深深地了解孤独。
昨晚的脸孔,今晚的脸孔…… 世界到处是变形者。
Metamorphosis——蜕变,进入卡夫卡世界的关键字。
一切都在变形。
而我不想变形。
我还在寻找进入我世界入口的关键字。
提起我的皮箱,买到冬日廉价的机票,飞往布拉格,一个多小时竟飞离寒带挪威,住到了查理大学宿舍。冬日的查理大学教职员宿舍空荡荡,一个大房有四个小房,一个小房有四张床,整间大房只有我一个人睡,有时我会换床位睡,像是和很多人一起住似的。宿舍柜台女生每天朝我笑着,我总暗自叫她特丽莎——《布拉格之春》。
不必卡夫卡告诉我,我的人生过往的一切或者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告诉我了——千万不要去向别人索爱。
或许,这会儿连悲哀都要珍惜。死寂的眼睛,看着教堂朝圣的北欧子民,那样虔诚,主看见了吗?我不知道,但我看见了。
我躺在旅馆,看着自己这么多年的旅次,如同这古老宿舍破旧发霉的天花板,仔细地闻着像是窝藏好几个冬日的霉味,闻闻这一切的生活气味,或许我该高兴些。
坐在松软无力的床,吃着几天前路边买的马铃薯片,不脆了,但我却是智障儿般地一口接一口,无意识地一直放进嘴里。
我渺小地在异乡,再度想起挪威男子对我吼出的 “你这是哪门子的女性主义作祟”。我的黑发成了他的魅惑,他宛如提早得 “白化症”的苍白却治不了我的东方乡愁。
于是我坐在这里。
发呆,呆呆的感觉,在语言困顿的小城。冬日,竞只我一个东方客,真正的异乡人。几天后,偌大的宿舍来了个年轻的交换学生,哈利路亚!他会说英语。我跟他出游至温泉区,同一个旅馆房间却什么事也没发生。早晨,我见男人在阳台抽闷烟,我知道我再度让男人不解。
他无法明白我可以同游却无法有爱欲的冒险困顿,他无法明白囚禁我心的原乡情爱。
落脚的温泉小城,屋外星星很亮,亮在黑色的无光里,无隐低调的亮,我喜欢的光泽,暗暗地亮着,像认真的文学写作者,用孤寂的生命独自在书房的围城孤岛里完成书写,像星星一般,几乎少被见到。
独自在小山坡走着,小小的房屋墙面在白天看来很鲜艳的大黄或者大蓝之颜都隐去了,圣诞节过后的麋鹿或者圣诞老人或雪人雪橇都还闪着小灯泡,一闪一闪的,也很安静,让人目光看了感到一种很俗世的眷恋。窗户都放下了蕾丝窗帘,纱帘随着山风飘进飘出,我想象着睡在里面的人是孤单者或是双人枕头。他们的鼾声让失眠者听来是幸福之声了。
只任凭尘埃飞扬,这座温泉小城,连空气都飘扬着疲惫,古老得不得了的疲惫。
十分浅眠,钟声总是当当地不断响起。窗外傍着古老的美丽教堂,尖顶矗立对窗,前方广场已经安静下来了。这是一间十分孤独的旅店,冬日里,交换学生拎着行李对我告别,他换住处,我又一个人。望其背影,我想他比我更有自主能力。
我常不知道是何等的冲动导致自己把自己的肉身推离家门。
为什么我要一个人走在这块陌生的土地?挪威男人的家不也颇温暖吗?他说他永远都不明白我。我当然不是为了卡夫卡,这真实摆在我眼前的卡夫卡踩踏过的城市风貌,可让我闻得到古老悲伤的犹太人气味,也看见了层层古城在诉说着亘古不逝的死亡与忧伤。
我确实不为任何人,我是为了我自己而行走。
旅店窗外,石板路上一个美丽混血小女孩持着仙女棒对空正画着星星和花朵,我一个人退到墙边,挨着墙,打捞一些意识,觉得自己无论面临什么困境,总是还可以一直写很多字,走很多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自主与精神冒险。
如是自言:写作吧,只有写作可以不伤你的心。
一直写,一直走。
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