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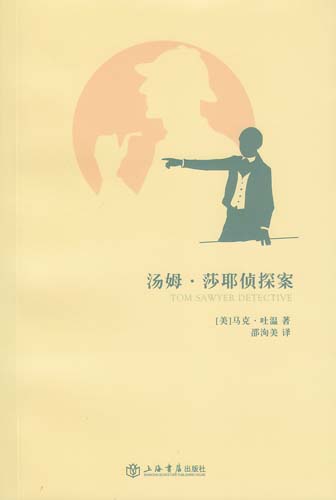 马克·吐温是十九世纪美国最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用亲切和幽默的笔调、深刻和辛辣的讽刺,暴露了资产阶级丑恶的生活和卑鄙的行为,获得了一般劳苦大众的热爱。他所写作的儿童读物,更成为许多小朋友们时常接近的伴侣——虽然成年人读了也一般地不忍释手。 马克·吐温是十九世纪美国最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用亲切和幽默的笔调、深刻和辛辣的讽刺,暴露了资产阶级丑恶的生活和卑鄙的行为,获得了一般劳苦大众的热爱。他所写作的儿童读物,更成为许多小朋友们时常接近的伴侣——虽然成年人读了也一般地不忍释手。
他的作品在一九五三年被美国的麦卡锡为首的参议院政府活动调查委员会(华尔街的思想警察机构)列入黑名单,不准图书馆出借,有些地方还公开焚毁。可是全世界的人民对于他的热爱却一天比一天深挚了;他的作品也先后译成了各国文字,增添了大量的读者。
这里所翻译的是他的两部中篇侦探小说。第一部是根据瑞典的IH案改写的,仍以两位大名鼎鼎的小朋友,汤姆·莎耶和哈克贝利·芬做主角,叙述一件错综复杂的谋杀案:这里面有匪徒的内讧、地主的阴谋、冤家的诬害,以及资产阶级统治下法律的腐败;并表现出汤姆·莎耶的聪明机智和爱好冒险的精神。第二部是一篇讽刺小说,嘲笑美国流行的侦探故事:一般侦探只知道“追求线索”,不肯观察现实,分析事理,以致牵强附会,错误百出。作者同时又尽情攻击当地不近情理的政治待遇,和那种惨无人道地滥用私刑的罪恶。
这两部作品一贯地表现出作者对压迫者的憎恨,对被压迫者的同情,以及对反抗精神和反抗行为的热烈的鼓励。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作品出版时的历史环境,正巧是美国资本主义勃兴又逐渐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作者那种歌颂自由的论调,无疑地要引起一般统治阶级的恐怖和厌恶。可是马克·吐温的作品始终有着占据人口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做后盾,吓得他们不敢公然破坏,只能用消极的方法,阴谋的手段,来歪曲它们的内容,来诬蔑作者的思想。他反对一般人对“黑奴”的非人行为,他们却说他是在宣扬黑人的驯良品性;他痛恨一般披着宗教外衣为非作歹的传教士,他们却说他是故意诽谤宗教;他赞美一般儿童有冒险的精神,不怕经历任何的艰苦,又能凭着机智去克服一切的困难,他们却说他是在劝导儿童要循规蹈矩,服从大人的教训:碰到那些实在无从曲解的地方,他们便又推说这是他的滑稽风格,根本开开玩笑,并无深刻的意义。但是聪明的读者是决不会受他们蒙蔽的,尤其是经过了苏联文坛一再给予正确的评价和热烈的赞美,所以许多年来,马克·吐温的作品,一直是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的读物。
在这两部小说里面,作者更是毫不掩饰地为被压迫者泄恨出气。他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说明:那所谓“正统的法律”惯常只会冤枉好人;被压迫者的反抗也一向要受到他们不顾事实情理的严酷的迫害。
他在《汤姆·莎耶侦探案》里把赛拉姨父写成是一个被压迫者:他受到地主恶霸的欺侮和威胁,神经都失了常态。在律师、恶霸地主和许多伪证人的共同合作下,他被他们诬告做凶手,亏得汤姆·莎耶聪明机警,一方面根据了当前的事实,一方面依靠过去观察所得的印象,汇集拢来,仔细分析,终于识破了对方的阴谋毒计,案情因之大白。
他在《双料侦探案》里,一共写出了三个受到压迫的人:第一个是约可伯·傅勒的新娘;第二个是约可伯·傅勒的同名同姓的堂兄弟;第三个是斐特洛克·琼斯。这三个人受到压迫的情形不同,所起的反应也不同;马克·吐温对他们的处理方式于是也各有不同。第一个虽然受到她丈夫非人的虐侍,但是她的报复完全出于自私的心理,因此作者没有让她达到她凶狠的目的。第二个受到的压迫,完全出于误会,可是他不敢反抗,一再逃避,他是一个十足的弱者,作者也并不如何看重。第三个受到他雇主经常的欺凌和迫害,甚至生命的威胁,他结果用了上一天仇人几乎把他炸死的炸药,将他的仇人炸死。但是作者强调着群众对他的同情和怜悯,甚至公开说要将他释放,因为那个危害人民的家伙是死不足惜的;结果把他关在一所没人住的小木屋里,让他一个人在那儿等候审判,终于被他“在晚上逃走了”。
这类字里行间的暗示,也是马克·吐温一贯的作风,时常使读者看了拍案叫绝,又把他所传达的意志永远印在脑子里。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克·吐温的作品,在鼓励反抗压迫、爱好自由和乐观主义精神方面,对美国人民是曾经起着一定的提示作用的。第一部的故事用哈克贝利·芬的口吻来叙述,译文因此尽量求其口语化。第二部是讽刺作品,译文因此竭力设法保持原文的风格。成绩和理想中间的距离,当然很远:希望读者多多指教,尤其欢迎小朋友们来提出宝贵的意见!
邵洵美
一九五五,九,二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