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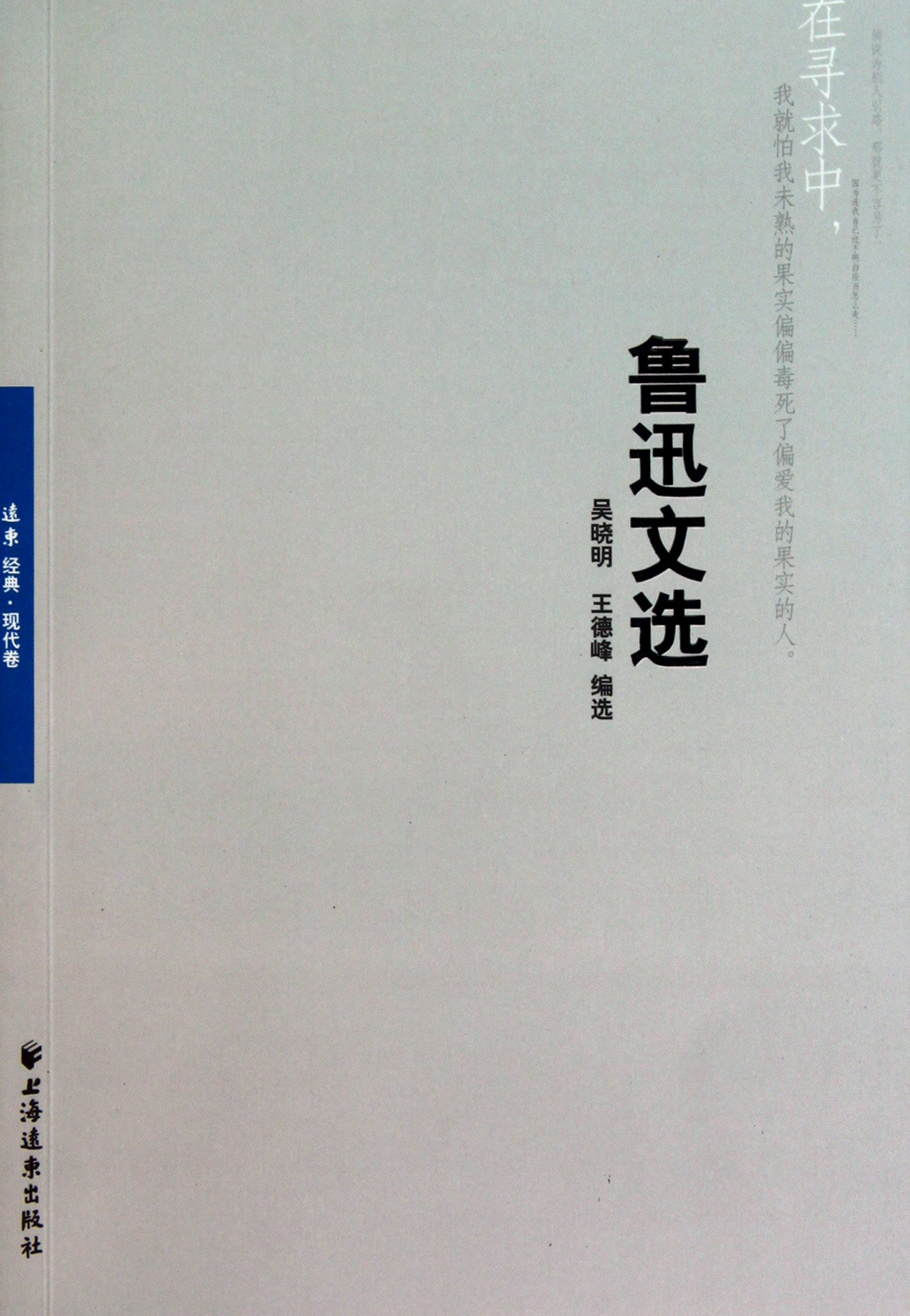 鲁迅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突出地位,是无庸在此赘述的。然而,对他的认识和评价,在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固定不变”的时期之后,于近来,渐渐生出颇大的分歧。这或许又是一个例子说明,当代中国人在以新的希望走向明天的时候,正力图再认识、再理解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精神历程。于是,我们感到有必要为鲁迅先生留下的文字编一部新的选本。着眼点自然在于为今日的学术研究而把资料再集中一下,所存的一点奢望,便是我们的选本或许能比已有的其他本子更清楚地反映鲁迅一生的思想脉络,以益于我们的文化讨论。成功与否,自待公鉴。 鲁迅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突出地位,是无庸在此赘述的。然而,对他的认识和评价,在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固定不变”的时期之后,于近来,渐渐生出颇大的分歧。这或许又是一个例子说明,当代中国人在以新的希望走向明天的时候,正力图再认识、再理解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精神历程。于是,我们感到有必要为鲁迅先生留下的文字编一部新的选本。着眼点自然在于为今日的学术研究而把资料再集中一下,所存的一点奢望,便是我们的选本或许能比已有的其他本子更清楚地反映鲁迅一生的思想脉络,以益于我们的文化讨论。成功与否,自待公鉴。
现在,文选已经编好,放在广大读者面前了,工作至此,本该算是做完了,无须更多的话。然而,由于我们和读者诸君一样,在经历了(或至少有一部分是耳闻了)那么多鲁迅本人未能经历的变故之后,重读鲁迅的文字,难免生出一些感想;有感要发,便顾不上担心浅陋,顺便将其写出,借此就教于大家,但愿不只是徒费着读者的目力和心神。
做史的意义全在于当代,做思想史自然亦是如此。对当代状况的见解是见仁见智的,而对于至少是较近之将来的展望,也是各有差异的,于是便在学界有热闹的讨论。讨论总得有所依据。最切近、最关紧要的依据并不是遥远的古代,而是才过去不久的一百年来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古老的中国经历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生大人物,其中不乏堪称今人之思想前辈者,他们曾以各自的形式提出自己的主张,甚或有亲自实践者。实践总是对思想的检验.。后人自然会以实践之结果去评价前人的思想,兼作现在讨论的依据。但是这样的依据是否绝对可靠,却总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对依据本身复有一个评价的问题,其中往往便隐藏着今人的选择;更何况,我们谁也说不准当下是否正是检验完成之时。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换一个角度,即看一看前人思想所由出发的问题,是否在今天还保持为问题。我们也应当如此看鲁迅的思想。
鲁迅先生对于现代中国的问题是否曾经给出过一些解决之方案?仔细读一下他的文字,可以发现:没有。他一生都在寻找着,但不是学术式地寻找着,而是在十分酷烈的现实斗争中寻找着。而现实斗争的严酷性似乎早已让他体会到这种寻找本身是希望渺茫的。这有他自己的话为证:“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写在(坟)后面》)鲁迅平生极厌恶以“青年的导师”自命的那些人。这显示了鲁迅思想的深刻之处,这种深刻性是我们在其他的近代思想先辈身上所未曾见到的。或有论者提出异议说,这不正是鲁迅由其一段时期中的彷徨、苦闷所引出的暂时的虚无主义吗?但这种说法是肤浅的贴标签方式,不足为训。鲁迅的彷徨苦闷原非一时的心态。他早期的《文化偏至论》一文即已表明他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向往的“西方真理”并无乐观态度。他在这篇写于1907年的文章中批评了只见到西方物质文明与民主政治为强国之本的浅陋见识:“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指物质文明、民主体制等]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在鲁迅看来,根本要务在于彻底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使之从旧文明的_枷锁中解放出来,获得一种新生命,是为“立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文化偏至论》)。但是,如何立新的中国人?鲁迅对此却是毫无把握的。西方的立人之本能否移至中国?他曾经写道:“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致宋崇义信》);“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忽然想到〈一至四〉》);“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被共和二字所淹没”(《灯下漫笔》);“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偶感》)。既如此,那么回归中国精神传统,取其精华而新之,是否可以成为改造国民性的一条道路?鲁迅对之予以坚决的否定。假如这种精神传统是指中国古代先哲之教训,则鲁迅断然指出:这种教训与中国民众“毫无亲密之处”,是中国自古以来统治阶层的治民之术,而围绕这种治民术建立起来的文化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假如这种精神传统是指活生生地存在于中国民众身上的东西,那么它就是“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的国民性——“懂得此理者,懂中国大半”。这写在《小杂感》一文中的寥寥数语,在解剖民间精神传统方面是何等深刻!另外,我们还不要忘记了鲁迅曾多次十分沉痛地鞭挞过的中国人的看客态度!这一切在某些有名声的大学者那里往往是当作无伤大雅的现象而被忽略了的,但是,对于鲁迅来说,乃意味着无底的黑暗与压迫,是要窒息一切生机的。因此,就何处寻得立新的中国人的文化精神资源的问题,鲁迅是并无把握去回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