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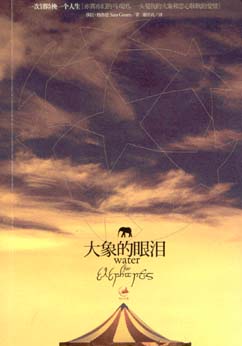 把美国女作家莎拉·格鲁恩的小说英文名“Water For Elephants”翻译为《大象的眼泪》,其实并不怎么准确,结合书里的内容,应该译成“喂大象喝水”才更恰当、合理。“大象的眼泪”这个说法,从语法角度来解释有些牵强,可能是中文译者想让它摆脱那土气的面目,变得诗意一些、美化一些,就像作者把那黑暗倒霉的社会“伪装”得温情脉脉一样。 把美国女作家莎拉·格鲁恩的小说英文名“Water For Elephants”翻译为《大象的眼泪》,其实并不怎么准确,结合书里的内容,应该译成“喂大象喝水”才更恰当、合理。“大象的眼泪”这个说法,从语法角度来解释有些牵强,可能是中文译者想让它摆脱那土气的面目,变得诗意一些、美化一些,就像作者把那黑暗倒霉的社会“伪装”得温情脉脉一样。
有“眼泪”二字,并不表示这部小说就是一个“悲剧”的结局。它以上世纪30年代初美国的大萧条为背景,叙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23岁的主人公雅各因父母车祸身亡,而所有的财产又因银行倒闭而消失,他被迫流落到马戏团做兽医,结识了玛莲娜,并对她一见钟情。美丽而又楚楚可怜的玛莲娜已经错嫁给了外表英俊、内心残暴的马戏团总监奥古斯特。对雅各而言,马戏团是他梦想的驻扎之地,也是他流离失所的开始。
然而,当我把本书读到将近一半时,却没有见到一头大象的影子,更别提大象的眼泪了。那头大象是后来的事情,雅各的马戏团收留了大象萝西,但它只能听懂波兰语,没法参加团里的演出,低鸣、哀哭、长嚎,萝西每日在奥古斯特残暴的象钩下受尽折磨,它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雅各和玛莲娜也都成了受害者。而雅各对于玛莲娜和萝西的深情是类似的,萝西所受的皮肉之苦如同玛莲娜忍受丈夫的暴躁善变,解救萝西等同解救玛莲娜,解救玛莲娜等同救赎自己。于是,这两个人开始“策划”一场逃跑,在动物全数奔逃的过程中,大象萝西却意外杀死了奥古斯特——而唯一目睹这一切的雅各把这个秘密隐藏了70多年……小说用“倒叙法”诉说了关于秘密与承诺、爱与信任——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让大伙感受到困顿景况里最动人的温暖。而那岁月的回顾与交错,更像是奥德丽·尼芬格《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与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的结合,情感与回忆并济。
故事的另一个亮点在于马戏团,几百斤重的女人、浑身刺青的汉子、侏儒、畸型人……马戏团靠稀奇古怪吸引人,容纳了酒鬼、野蛮人、打手、小偷、妓女,它就像是一个边缘人的大集会,就是我们常说的“江湖”。江湖不相信眼泪,你有能力、能工作就有吃的、喝的;“健康”和“年轻”是他们生存与发展的资本,老了、残了、碍手碍脚了,就会在巡演途中被人从火车上丢下去,连尸首都找不着……在这里,畸型人与小丑轮流献艺,喜怒哀乐同时上演。
在大萧条那样极端的环境里,景况愈加恶劣。光提供动物们喝的水,就足以让一个人破产,人为了基本生存,要抢地盘、抢饭碗。马戏团的巡演专用火车越发拥挤,人和动物开始混住,少了“界限”,就连“行为准则”也开始模糊起来。团主恶意克扣艺人的工钱;总监变本加厉折磨动物,催逼它们演出;“废物”们在月黑风高之夜被丢下火车;巡演地的警察还经常找上门来,一边要着保护费,一边驱赶着这些可能引来乱子的家伙们。
好像一切都是“混乱”的,人的“理性”和“人道”都被丢进了食物桶,送到了笼子里的狮子、老虎口中。马戏团盛大的表演场面光鲜无比,可谁会料到幕后遍地狼藉?观众走入大帐篷,只为火圈、飞镖和钢丝叫好,可谁为帐篷外暗影中哭泣的小工留下“一声叹息”呢?在那样糟糕透顶的世界里,人性之光还能闪现一下吗?作者说:能!但总要付出代价。雅各和玛莲娜慢慢萌生爱意,大象萝西渐渐博得团员们的同情,一向敌视雅各的艺人也成了他的铁哥们儿——如果这一切不是伴随着奥古斯特的虐待、团主的威逼,不是与死亡同乘一列火车的话,那一定会温情、友好得多。
我发现,通俗小说作家都有个“坏习惯”,刚刚发觉自己“残酷”过头,就赶忙扳下道岔,让火车走上正轨。雅各、玛莲娜和大象萝西到底还是过上了新生活,一部冒险片在高潮后归于平静,一切都是那么“好莱坞式”,让人讨厌。我宁愿它冷酷到底,好带着倏然心惊重新面对这个社会,知道在某个角落里还滋生着怎样的恶之花。然而,主角要摆脱枷锁,求得人生自由——作者就必须写得符合“人”的典型世界观。既然这样,大伙喜欢这本书也就不奇怪了。我只能说格鲁恩挺会讲故事,但要想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和警示,她还得再“狠心”一点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