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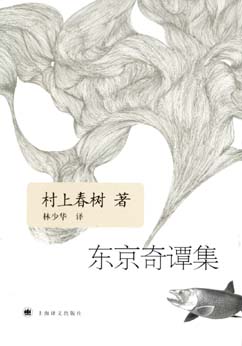 写小说的人都会写着写着把家人、朋友身上的故事写成或者写进小说,听到好故事总抑制不住要写出来的冲动。“对我来说,只不过被某种不可思议的事打动而已。心想,这样的事情,是真的会发生啊!”村上春树说。于是,他一气讲了五个故事:《偶然的旅人》、《哈纳莱伊湾》、《在所有可能找见的场所》、《天天移动的肾形石》、《品川猴》,里面的人无不生活在东京,有复杂的人名、真切的地名,即使看似不够确凿,也会用证人和其他现实元素增加他们确实存在的可信度,可情节还是忍不住从那些可能就在身边发生过的、可能是错觉又可以理解成神谕的小事,逐步发展到会说话、会盗窃名字、还讲点儿人生百味的猴子出场的地步,却嘎然而止。 写小说的人都会写着写着把家人、朋友身上的故事写成或者写进小说,听到好故事总抑制不住要写出来的冲动。“对我来说,只不过被某种不可思议的事打动而已。心想,这样的事情,是真的会发生啊!”村上春树说。于是,他一气讲了五个故事:《偶然的旅人》、《哈纳莱伊湾》、《在所有可能找见的场所》、《天天移动的肾形石》、《品川猴》,里面的人无不生活在东京,有复杂的人名、真切的地名,即使看似不够确凿,也会用证人和其他现实元素增加他们确实存在的可信度,可情节还是忍不住从那些可能就在身边发生过的、可能是错觉又可以理解成神谕的小事,逐步发展到会说话、会盗窃名字、还讲点儿人生百味的猴子出场的地步,却嘎然而止。
相比之下,眼前这本《东京奇谭集》已经不再有那种火山岩浆默默地流着流着将人吞噬,慢慢流着流着又凝固不动的感觉了,类似的情绪还在,却忽而少,忽而多,轻重火候总有些不够合适。在豆瓣网上,仅给四星的人要比打五星“力荐”这本书的人多一倍多。我揣测,村上春树自己也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他在小说里写出“刚下笔时觉得似乎可以写出漂亮的东西,行文生机勃勃,前景如在目前,情节自然喷涌,但随着故事的进展,那种气势和光芒开始一点点地失去,眼睁睁地看着它失去”这样的句子。但他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丢下面包屑把读他故事的人带到那个情景里,静静地听他讲,不断回忆自己生活中是否有类似的经历:“是啊,我曾想起过某个多年没联系的人,他/她也正急着跟我联系”,“我也看到过明知不可能在那儿的人,不,那不是幻觉”,“其实我正在经历一段搅动我生活的恋爱”,“我也会忘记自己的名字,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几乎每个人都能在这几个故事里找到自己记忆的附着点,胡思乱想一阵,有所感。
只是,我在看了《在所有可能找见的场所》之后,想讲一个故事的愿望变得非常强烈。
我舅舅的一个同事,参加了春节前的单位聚餐后回家,情绪愉悦,滴酒未沾,不到晚上十点已经从长安街开车直到自家楼下,接了她先生打来的电话,回答说:“我就上楼了。”她先生也眼睁睁地撩开一半窗帘从楼上看着她停车入位,随后坐下边看电视边等她上楼。可一等几个小时,然后是几天,她再也没有上来。这一失踪,快8年了。所有人、所有地方都找过,报了案、立了案,连我舅舅都被带去派出所录了证词。据说做丈夫的到现在也没放弃,只是拆了家里电话,深怕有一天电话铃响起是为了告诉他河边有一具女尸,你来认认吧。
我远不如村上春树讲得动听,只是它是真的。
我暗暗希望她能像村上故事里那位先生一样,在某天出现在某个地方,活着,就算记不得这么多年的事,甚至根本记不得以前。她只是不慎掉入了空间与空间之间没闭合好的缝隙,她不得不经过长长的扭曲的通道,从另外一个小口儿里钻出来,那个出口即使不在仙台,在广州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