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到目前为止,在古代异教徒世界中广为人知且广泛制造的那类雕像中最伟大的、其实也是硕果仅存的一例:英雄,权威人物,马背上的半神;人类的智慧与力量驾驭着动物王国,大获全胜、昂首向前。
在罗马,曾有约二十座这样的青铜骑马像,整个意大利则有更多,譬如帕维亚的“太阳王”——在1796年遭毁坏殆尽,一片不留,唯一尚存的痕迹只有一张纸上的木刻版画。
只有马可·奥勒留的雕像阴差阳错地幸存了下来。那是因为忠心耿耿的天主教徒误将其当成了罗马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的骑马像。
要不是由于这撞了大运的误会,马可·奥勒留也早已与其他青铜皇帝一起进了历史无情的熔炉。
当然,在那个1959年的夏夜,刚满二十岁的我对此近乎一无所知,我第一次见到这位青铜骑士,米开朗琪罗的元老院宫(Palazzo del Senatore)隐约闪着金光、衬托着它黑暗的色泽,蝙蝠开始在周围掠过。我对马的了解更少,不管是老马新马、假马真马。
我是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只在灌木地带逗留过几次,于我而言,马这种动物就是“从头到尾写满了‘危险’二字”。一想到爬上一匹14掌宽高的马就使我老大不情愿,甚至心怀恐惧。
然而,当我绕基座而行,感受着那由一人一马的身躯与四肢所带来的空间与形状改变所带来的恢宏气势时,我意识到,这马匹与骑士无可比拟地超越了我之前所见的任何雕塑,甚至是任何艺术作品。
澳大利亚或许也有一些骑马青铜像——可能是战争纪念物?——不过即使是有,我也记不起来了。大概根本没有,因为制造一座真实尺寸的青铜人像、再加上青铜马,需要耗费大量的金属,在一个没有公共雕塑传统的国家实在是过于铺张了。其制作还需要专门的铸造厂与特殊的工艺,而在我的家乡,以上的哪一项都是难以得到的。
不过真正使马可·奥勒留与他的坐骑在我极为有限的经历中如此独一无二的,是其对雕塑之庄严宏伟与细节之深入刻画的融汇。
你可以制造一匹普遍意义的高头大马,以及一个真实尺寸的典型的人物,而不能唤起更精细的雕塑所能产生的那种感受。
但这体现不了马可·奥勒留雕像所传递的东西,那种对聚沙成塔、江河入海的热烈领会,那种在更广阔的生命图景中,将细节咬合在一起的秩序井然的积累。
这可不是一匹摇摇木马:套着金属马衔的马嘴在缰绳的拉力下紧紧收拢、痛苦变形;它看起来凶猛暴烈,却又证明着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
马可·奥勒留的头发精力充沛地竖起,一绺绺鬈曲起来,仿佛形成了一圈光轮,与许多罗马大理石像上表现头发的惯常形式大相径庭。
他前伸的右手做出平息一切的手势,既威严高贵(正是一只帝王之手所该做的),又和蔼仁慈(如同一位斯多葛派信徒那样;正是这只手写下了马尔库斯的《沉思录》)。
雕像四肢各不相同的伸展方向经过调节,呈现出互相竞争的态势,马匹抬起的左前腿与骑跨着它的人张开的双腿相互衬托,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运动之感。还有色彩。青铜承载着两千多年的绿锈。这是使用化学品所无法复制的。
它讲述了一段长久暴露在风吹日晒中的故事,超过二十多代人类生存的岁月,每一代人都在它尊贵的表面留下了几块补丁、数点金斑、几条绿痕与点点污渍的负担。
在我第一次见到马可·奥勒留像时,这一过程早已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就像以极为缓慢的速度酿制葡萄酒,历经了悠久的时光,以不同的规模同时陈化着米开朗琪罗为这一人一马所造的建筑框架——基座渐渐起皱的轮廓,以及元老院宫由光彩照人至光阴渐染,终于成熟芳醇的表面。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鲜有对往事的兴趣——往事似乎是如此遥远,与己无关,且还在方方面面充斥着失败。未来也是同样地难以想象;你会被无数种可能性写就的传奇淹没。
然而那却是罗马对年轻时的我所施的魔法。这座城市既领我向后回顾,也引我向前眺望。它带我洞察美丽与毁灭,悟悉胜利与灾难。最重要的是,它为艺术的概念带来了现实的形态,不单单像精英们口中那般虚无缥缈,而是充满了启发性,甚至功利性。
于我而言,那是平生头一遭,罗马从艺术与历史变为了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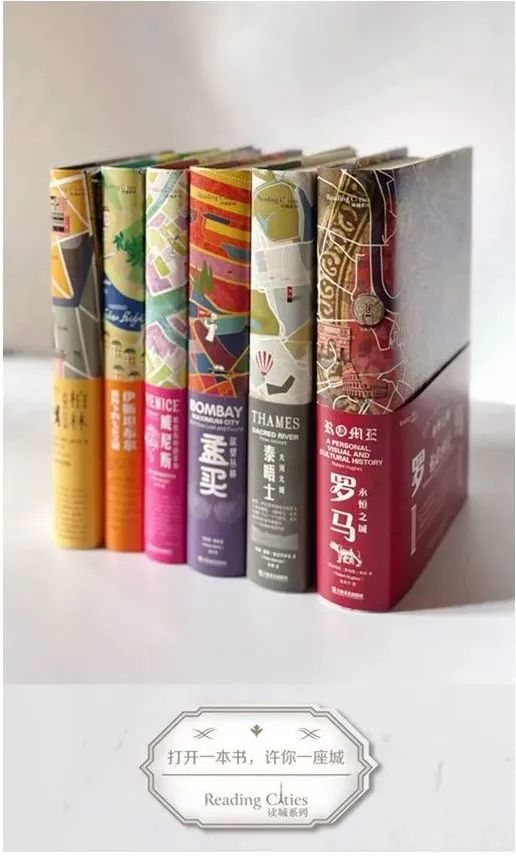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