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1日早,书评君推毕戴锦华和汪民安对谈纪录片《米歇尔·福柯》的现场稿,收到了读者评论:“相比别家公众号发送的原汁原味现场记录,本文抓取几个特写镜头,提炼归纳并融入一些思考,轻巧幽默更耐品。”即便经常被鼓励和肯定,但看见这段话仍遏制不住感动。
这篇稿子并不特别,这些年我们一直走在这个方向上:“阅读需要主张”,始终同简单粗糙的“程式化”保持距离。我们关注个体,做出严肃的反思,但也陪你一起在喧嚣和不确定的年代感受世界的新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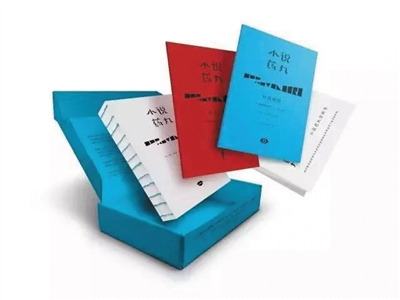
个体的情绪
年代赋予了“我们”共同的特征
法国作家夏尔·丹齐格说:“杰作是一部把我们变成杰作的作品。一旦它穿过了我们,我们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们了。”这里的“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互不相干的生命走向了群体认同,因在文字或图画里被触动了相似的记忆而意识到彼此真的是“我们”。难怪在学术界经常用一个词叫“同期群”,含义很简单,用来概括生于或成长于同年代的群体,假设他们面临相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可能具有类似的特征。
《独生小孩》 我们在25日关注到一本叫《独生小孩》的铅笔画绘本,推送了《这个中国的独生小孩为什么被全世界一见钟情?》。绘本的作者郭婧生于80年代,是一个独生姑娘,用铅笔画的方式,记录了80、90年代独生子女共同的童年记忆、孤独和期望。我们专访郭婧,探寻了她自身一段自我追寻的漫漫征途。
文章在当天便获得七万的阅读量,不管是“眼泪不知不觉流下来,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独生小孩”,还是“看完每一幅暖心而又略带忧伤的话,不经意间触碰到了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读者留下的评论,见证了他们的内心感触,共同在文字和绘图中感触到“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个体境遇。
不管怎样,郭婧在绘本中的主人公在去姥姥家的路上走失了,经历了一段奇特的冒险后,顺利回到了家。这一段路,在成年毕业后可能有点模糊了。即便完成了高等教育,我们仍然在北上广深上下班高峰的地铁上,目睹了那些匆忙的年轻身影。西装革履,抵挡不住疲惫的眼神。做着体面的工作,拿着过万的月薪,却仍然挣扎在城市基本的生存线上,被称“高薪穷人”。
“高薪穷人” 我们在24日推送的《“中产”虚幻而焦虑,你是那个高薪穷人吗?|十问》就此对话学者李春玲,谈中产的面孔。上中下层的中产分离严重,而下层中产,特别是生于80、90一代仍挣扎在迈入中产的队列中,社会给予的流动渠道已变窄。我们收到“中国没有中产,只有穷人富人之分”,“没有社会的保障……谁都有可能秒变穷人”等简短评论,仍可感受到难以抑制的焦虑和不安。
社会的反思
多元和平和的认识见证了进步
因“我们”的形成,原来那些问题和困惑不是一个人所有的,还有彼此不相干的个体因而可能形成共同的意识或行动:呼唤政策制定的生命关怀,呐喊社会资源和机会的不平等。在马克思传统的思想脉络里,这样群体被称之为“社会”。这里的社会是自由的联合体,为了共同的目的和利益而行动,同“国家”和“市场”组成大社会的三大领域,始终抵抗两者的权力和资本的伤害。
“碧山计划” 这种抵抗有何内涵?上世纪末城市化建设运动袭来后,农村走向了“凋零”,劳动力迫于生存的需要到城市务工,留下老人和儿童,变成学者说的“无主体社会”,而一些怀揣自身理想和想象的知识分子决定抵抗市场资本,挽救农村。我们在20日推送的《中国乡村,能否成为我们的乌托邦?》观察了前些年饱受争议的“碧山计划”。知识分子与乡村建设的渊源早在五四时期就有“新村运动”,意图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但都走向了失败。到底是理想主义,还是知识分子不明社会运作的真实原理而将自身的想象寄托于农村?
大概这是一个有点沉重的话题,阅读量没有上去,但读者留下了丰富而认真的评论。他们赞誉“只是失败了而已,但他们是仍敢于探索的人,不像我一样的某些人,没有勇气和能力去反抗”,而一条说“集体装逼”的评论也引来了大家的争议。不管如何评价,农村建设历来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而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却也很难扎根。我们觉得欣慰的是,在评论区,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声音在讲述复杂的农村,远非单一的理想主义所能及。这种多元的反思本身正是进步的见证。
排华史 但这种共同行动,在更大的时空下,还可能被民族主义或种族歧视导向不同的方向。中国在十九世纪多难,而在美国做低端工作的华工遭遇到了今天可能已被遗忘的排华史。我们在20日的《美国华裔编辑被斥“滚回中国”之前,有段被遗忘的排华史》整合书籍,回顾了这段历史,他们一致的行动,既有尤里卡镇的排华范式,专讲“和平”、真暴力,也有特拉基镇的排华方式:血腥的清洗与冷冻式的排挤。文章得到了读者的评论,尽管响应不大却很宁静。不能轻率猜测其中的原因,但既可以说历史被遗忘,或未被关注,但也可以说看到了一种心态:我们铭记历史,铭记曾经被迫害的生命,但这并不阻碍警惕偏激民族主义对历史的偏执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