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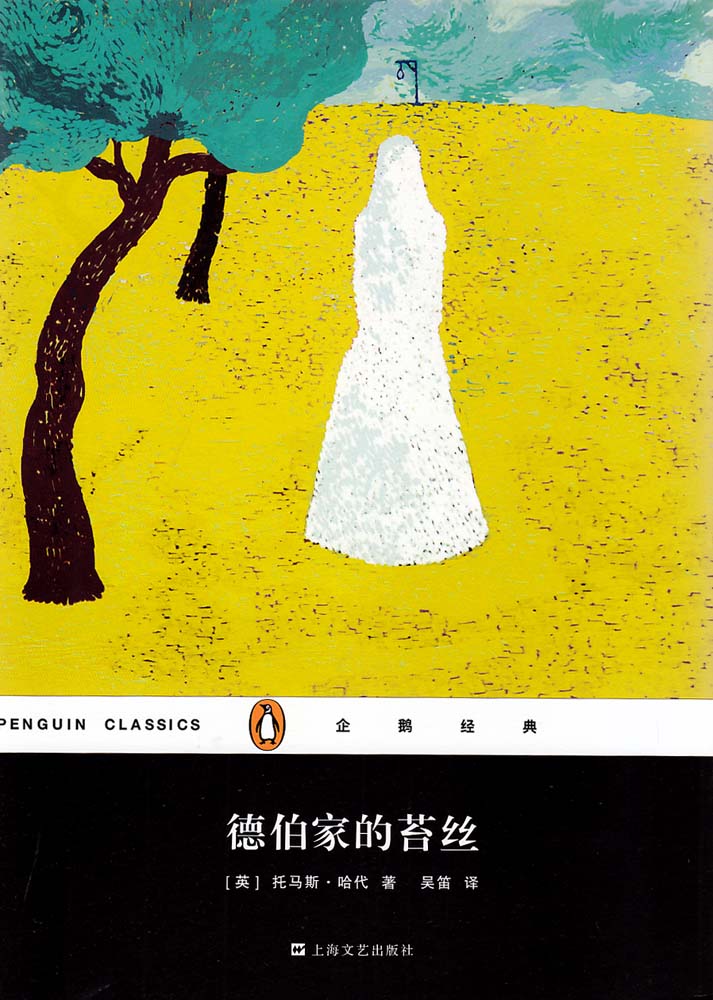 这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在主要活动展开之前,就经历了一个事件,人们通常认为,有了那番经历的女人是没有资格担任女主人公的,或者至少认为,那个事件实际上断送了她的前程和希望。可是,如果读者喜爱这本书,并且赞同我的观点,认为对于一件人所共知的悲惨事件,就它的隐秘方面而言,在小说中可以叙述的内容,要多于人们已经说出的东西,那么,就和公认的习俗完全背道而驰了。然而,《苔丝》在英美读者中也确实引起了共鸣,这似乎证明,按照人们心照不宣的观点进行写作,而不是恪守人们仅在口头上高谈阔论的社会习俗,也并非一无是处,即使使我是以高低不等的局部成就举例说明,也是可以这么说的。我禁不住要对人们的这种共鸣表示感谢。在这个世界上,渴望友谊的,常常只能枉然叹息,只要不被别人故意误解,也就算是受宠若惊了,而我却有幸遇到了这些厚意欣赏的男女读者。遗憾的是,我永远不能同这些读者一一见面、一一握手。 这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在主要活动展开之前,就经历了一个事件,人们通常认为,有了那番经历的女人是没有资格担任女主人公的,或者至少认为,那个事件实际上断送了她的前程和希望。可是,如果读者喜爱这本书,并且赞同我的观点,认为对于一件人所共知的悲惨事件,就它的隐秘方面而言,在小说中可以叙述的内容,要多于人们已经说出的东西,那么,就和公认的习俗完全背道而驰了。然而,《苔丝》在英美读者中也确实引起了共鸣,这似乎证明,按照人们心照不宣的观点进行写作,而不是恪守人们仅在口头上高谈阔论的社会习俗,也并非一无是处,即使使我是以高低不等的局部成就举例说明,也是可以这么说的。我禁不住要对人们的这种共鸣表示感谢。在这个世界上,渴望友谊的,常常只能枉然叹息,只要不被别人故意误解,也就算是受宠若惊了,而我却有幸遇到了这些厚意欣赏的男女读者。遗憾的是,我永远不能同这些读者一一见面、一一握手。
我说的这些读者,包括多数评论家。他们慷慨大方,对这部小说表示喜爱。从他们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他们和别的人一样,用自己的富有想象力的直觉,大量地弥补了我叙述方面的不足之处。
此外,这部小说的出发点既不想教训别人,也不想攻击别人,在描述部分,只求简单明了地表达意思;在思考部分,多记印象,少写主这种令人感激不尽的话语来表示他对作者的原谅。我可以很有把握地告诉这位伟大的批评家,五条无理地公然责怪一神或诸神,并非像他所想象的那样是我的“原罪”。的确,这也许有一些地方根源。然而,如果莎士比亚是一个历史权威(大概不是),我就可以指出:那种罪孽早在七国时代就被引进威塞克斯了。在李尔王的故事中(也可以说是在威塞克斯国王伊那的故事中),格罗斯特曾经说道:
天神对待我们,就像顽童对待飞虫,
他们随心所欲地宰割我们。
其余两三位攻击《苔丝》的人,都是那种先存偏见、为大多数作家和读者所乐意忘却的人,他们以“文坛拳师”为业,间或装出颇有信心的样子,要做现代的“惩治异端的铁锤”,发誓要把别人打得一败涂地,他们伺机行动,不让别人暂时的部分成功变为日后的十全十美的成就,他们歪曲一目了然的原意,并且打着运用伟大的历史方法的幌子,对个人进行攻击。他们也许有自己必须推行的目标。有必须维护的特权,有必须遵循的传统习俗;然而,一个讲故事的人,仅仅记录世上事物对自己产生的印象,别无其他用心,对于以上这些东西,自然也就未加注意了,而且可能纯粹出于疏忽,在毫无挑衅的情况下,与这些东西发生了冲突。也许,在梦幻时刻所产生的倏忽即逝的意念,如果普遍地实施起来,那么,将会使这样的攻击者在地位、利益、家庭、奴仆、牛、驴、邻居或邻居的老婆等等各个方面③遭受相当的麻烦。他因此勇敢地躲藏在出版者百叶窗的后面,高声叫喊“不要脸!”这个世界也实在太拥挤了。无论怎样挪动位置,哪怕是最有正当理由地向前挪动一步。都会触痛别人脚跟上的冻疮。这样的挪动时常始于感触,而这样的感触有时则始于一部小说。
一八九二年七月
前面那些话是在本书问世后不久写成的,那时候,对于本书所进行的公开和私下的激烈批评,在感情上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既然那番话已经说出来了,那么,不管它们是否具有价值,也仍旧保留在此了,若是现在,我恐怕就不会写出那样的话了。尽管从本书初版到现在,逝去的光阴还极其短暂,但是,惹起我作出上述答辩的那些批评家们,已有一些“人寂”了,这仿佛要提醒我们,无论是他们的话还是我的话,反正都已经无所谓了。
一八九五年一月
现在这一版的小说增添了好几页以前各版所没有收入的内容。在我把分散的章节收集在一起的时候(如我在1891年的出版说明里所陈述的那样),这几页被疏漏了,但在原稿里却一页不缺。这几页的内容出现在第十章里。
至于副标题,前面已经说及,现在可以补充的是,这个副标题是我在看过校样之后的最后时刻才加上去的,作为一个胸怀坦荡的人对女主人公所作的评判。我当时以为,对于这种评判,谁也不会驳斥的。谁知,对这几个字的驳斥超过了对书中任何内容的攻击。一字不写,效果更佳。不过,既然写了,还是留在书上吧。
这部小说于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分三册首次全部印行。
哈代
一九一二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