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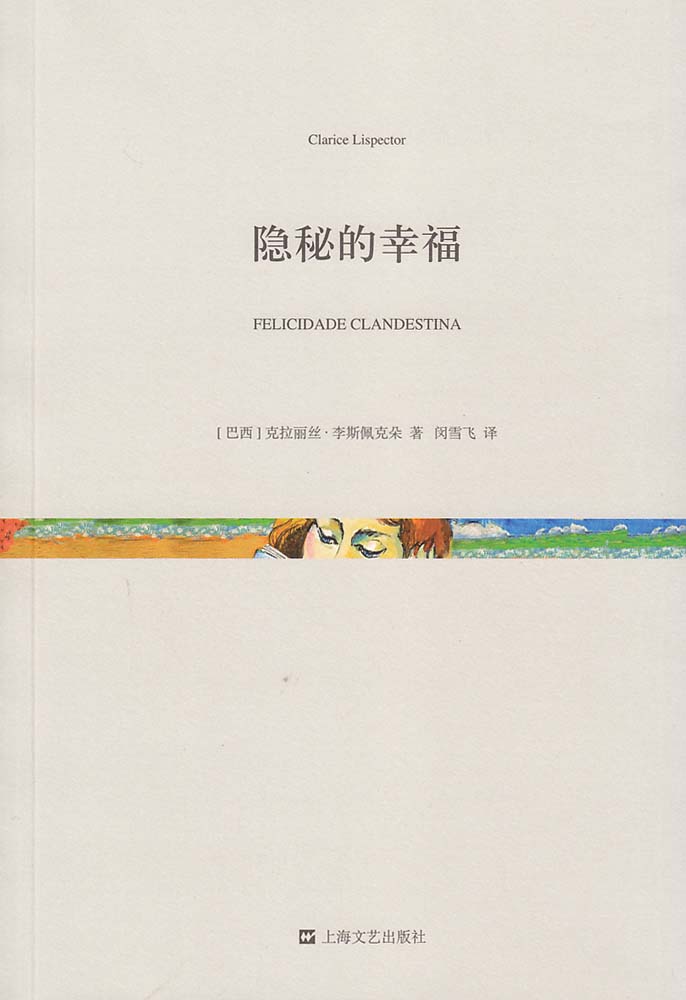 因为神秘莫测的命运,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偶然地”成为了葡语作家。她本该成为一位俄语作家,因为她出生在后来归属苏联的一个小小的乌克兰村落。她也可以成为英语作家,倘若美国的亲戚先给他们一家人发出了邀请函。她也可以如同辛格一般用意第绪语创作,因为她是犹太人的后裔,家中说意第绪语,父亲是一位犹太信仰的践行者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然而,因为神圣的命运的意志,她的父母决定移民巴西,尚在襁褓之中的她来到了南美,归化为巴西人,终生以葡萄牙语作为书写语言。 因为神秘莫测的命运,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偶然地”成为了葡语作家。她本该成为一位俄语作家,因为她出生在后来归属苏联的一个小小的乌克兰村落。她也可以成为英语作家,倘若美国的亲戚先给他们一家人发出了邀请函。她也可以如同辛格一般用意第绪语创作,因为她是犹太人的后裔,家中说意第绪语,父亲是一位犹太信仰的践行者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然而,因为神圣的命运的意志,她的父母决定移民巴西,尚在襁褓之中的她来到了南美,归化为巴西人,终生以葡萄牙语作为书写语言。
甚至连她的出生也全然是一种“偶然”。如果不是因为她的母亲得了怪病,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本来不会出生。当地人认为再生一个孩子可以治愈这种病。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携带着这个伟大的使命出生,然而她并没有成功:母亲的病终身不愈,直至死亡才让她得到解脱。或许正是因为自身生命这诸多的神秘与偶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才会终身通过书写探索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存在。
一九四三年,她发表了处女作《濒临狂野的心》,获得了巴西文学评论界的盛赞。评论家安东尼奥·甘迪特与塞尔吉奥·米利埃先后撰文,认为这部作品的语言非常独特,叙事技巧也很新颖,呈现出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地域小说”截然不同的风格。著名评论家阿尔瓦罗·林斯阿尔瓦罗·林斯断言这部小说是伍尔夫与乔伊斯的文学传统在巴西的第一次“经验”。虽然他称赞了克拉丽丝的写作风格新颖独特,但却认为这种没有开头、中段和结尾的小说在结构上不完整,她的创作是一次“不完整的经验”。这种批评暗指克拉丽丝对伍尔夫和乔伊斯不成熟的模仿,遭到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强烈反对,她当时便写信给阿尔瓦罗·林斯,表明虽然“濒临狂野的心”这句话出自《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一书,但这是朋友的建议,在她写作这本书之前,的确没有读过乔伊斯,也没有读过伍尔夫。
今天,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在巴西国内与国外均实现了充分的经典化,经过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我们可以洞悉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开拓性意义,而阿尔瓦罗·林斯的这番即时的“印象式”评价仿佛是一位伟大评论家偶然的失手。这样的事例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尤其发生在开创风气的作家身上。阿尔瓦罗·林斯看到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新颖,但是他无法去为这种新颖提供解释,更无法为她在巴西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准确的位置。反倒是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安东尼奥·甘迪特敏锐地发现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独特语言与风格产生的原因:这便是使葡语在思考这个层面获得延伸与增长。在散文《葡萄牙语》中,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将葡语定性为一种“不擅长思索”的语言,她的独特语言运用与写作手法完全是为了挣脱葡萄牙语的桎梏,这是一种必需,而不是单纯的模仿。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提供了一种新的资源,让葡语这一种“不擅长思索”的语言在抽象与形而上学的维度上获得了新的发展,这是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为葡萄牙语一这偶然成为她的母语的语言——所做出的第一个贡献。或许,正是执着地找寻存在与坚持在思考层面上展开书写让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具有了与乔伊斯及伍尔夫“偶然的”相似性。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为葡语与巴西文学所做出的第二个贡献,便是对文学主题的拓展。十九世纪末期,巴西文学巨擘马查多·德·阿西斯不满足于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文学(注:这种与印第安人神话联系紧密的文学形式正是我们中国读者尤其熟悉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通过其高度发展的现实主义文学,为巴西文学开辟了一条城市文学的新道路,从此,巴西作家知道了如何不去状写巴西的奇异风光便可以书写出“巴西性”(aBrasilidadesempitoresco),这正是巴西文学的独特性,在拉美的西语国家文学中,城市文学未曾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同样不去状写巴西的风景,她让当时流行“地域主义”的巴西文坛看到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要求作家去探寻人类最为幽深的内心世界。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通过她的尝试,向所有人证明,全然向内的书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写作,甚至是更为真实的现实主义写作,这种“现实”或者“真实”不是能够表现(represent)的,而是要通过对语言的复杂运用使其揭示(reveal)出来。而且,克拉丽丝的创新并不止于此,从她之后,主题不再是一个让巴西作家焦虑的问题。对于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无所谓好的主题或坏的主题,也没有大的主题与小的主题,在对事物真实性的探察中,她消灭了所有二元对立,对于她,一切都可以成为主题:一枚蛋、一只蟑螂、一只死去的老鼠。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之所以消弭了主题之间的差异,是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够将飘浮于人世间的存在之真实表达出来。表达是真正重要的事,也是非常艰难的事,因为真实无法表达,一旦能够表达,那就不再成为真实。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一生致力于通过各种方式,把她探寻到的真实尽可能真实地表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实现了罗兰·巴特所定义的真正的作家的使命:不去表达可以表达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