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干年前,一位四川的羌族老人对台湾历史学者王明珂讲述了过去村寨间经常性的暴力冲突和人们时时的恐惧,最后说道:“那是因为过去的人没‘知识’﹐不知道大家都是一个‘民族’”。
“这些话一直纠缠着我,它让我反思:为何我要解构这样的知识(使他们成为羌族的典范历史与民族知识),解构这样的民族?”王明珂的学术取径受后现代主义学风影响,曾相当具有解构性,但老人一句话的“纠缠”促使他对羌族研究的论述目的有了更深的理解:让人们知道本地人类生态由什么样的过去走来﹐并让人们思考,为了缔造更理想的明天﹐我们应往什么方向走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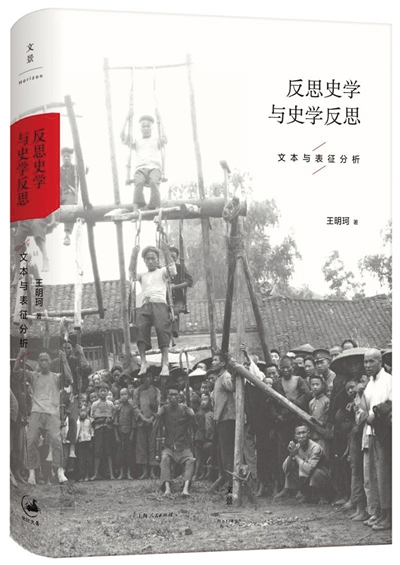
这样一种反思意识,在新书《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得以延续。结合史学与社会科学,他尝试解答的不只是历史问题、民族问题,也是社会现实问题——我们得自社会的历史与其他记忆如何影响我们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如何突破社会文化与学术教条施予我们的认知障碍和偏见?如何让个人基于反思性认知产生反思性行动,逐渐造成社会的良性变迁?
王明珂直白而真诚地将“历史”比喻为我们感觉麻痹的“脚底老茧”,但他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学术研究的目的是造就具反思性的个人。”于是,在这本论述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认识社会表相的书中,他在为读者抽丝剥茧,也在为自己寻找解构的彼岸。
拯救现实关怀
何为学术界的“武装走私者”?
新京报:你在新书中谈到,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的结合才是学术本分,但这种结合也很有可能变成自觉或不自觉的现实“功用”,你对当下学者的现实关怀有何判断?
王明珂:多年来,我在学术界见到过各种很失败的现实关怀作为。一种学者,顶着杰出学者光环及民众对他们的信赖,对所有公共事务都要插手关怀﹐无视那是否为自己专业。另一种学者﹐热衷于关怀现实﹐而忽略学术研究﹐因此其学养无法支持其解决现实问题。更普遍的是,学者积极投入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怀﹐而未能认识自身在此行动中的国家﹑民族﹑党派﹑族群﹑性别与社会阶级偏见,这样的偏见常扭曲其学术认知与逻辑思考。当然最糟的学术现实关怀便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与权位,以学术附和与支持社会威权下的不公义。
新京报:偏见是书中反思的要点之一,影响着现实关怀的有效性。你曾自喻为主动穿越、破坏边界的“毒药猫”,(“毒药猫”是流行于羌寨的一个传说:有些会法术的女人,晚上睡觉时灵魂会离开躯体,变成动物去害人。王明珂发现,这其实是人们创造的一个代罪羔羊,以此化解群体内部的紧张关系。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学界的“毒药猫”,穿越、破坏各学科的边界,挑战主流权威。)
跨界是消解学科偏见的一条可行之路吗?
王明珂:学者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要注意的是﹐此是否为自己的研究领域﹐自己的学术能否提供积极有效之意见﹐以及自己的参与是否受自身社会身份认同的影响。学术包装下的偏见﹐还包括学科自身基本法则﹑概念﹑理论产生的知识偏见。跨越学科边界﹐多了解其他学科思考问题的方法﹐反思自己所接受的教条式学科法则﹐能在相当程度上突破自身的学科偏见。对于各学科主流群体来说﹐跨界是不受欢迎的“毒药猫”。但对我来说﹐我自认为是“武装走私者”﹔这是一种自我警惕——要跨越学术边界私运知识﹐自己便先得有知识武装。
新京报:“跨界的武装走私者”是一种具有解构性气质的学者定位。你曾谈到自己的学术取径于后现代主义解构性学风,而大陆学术界在10年中断期后,在上世纪80、90年代后也大量吸收了后现代主义。这种解构性的风气是否在有效地促生社会的反思性思考和关怀?
王明珂: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快速且大量地吸收西方学界最新的研究﹐后现代主义中的解构﹑批判,以及跨越学科边界之风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但无论在国内或欧美﹑日﹑韩﹐经过多年对国家﹑社会﹑文化解构与批判后﹐社会并没有变得更理想。各国家﹑民族以及各文化体之间的敌意与冲突﹐因学者们对自身的认同偏见缺乏反思﹐相互解构﹑批判而加剧。这样的社会走向及因此造成的挫折感﹐让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无论在理论与行动上都更激进。
纠偏公共记忆
斑缘人如何撼动主流历史?
新京报:主流/边缘历史是新书中一对重要概念。你提及1995年前后美国史密森国家航空与航天博物馆的一场争议:对于所展示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轰炸机﹐应强调其对结束战争的贡献,还是强调日本所受到的巨大灾难﹖博物馆参与着公共记忆的塑造,但大多数博物馆所呈现的记忆都是“安全的”。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