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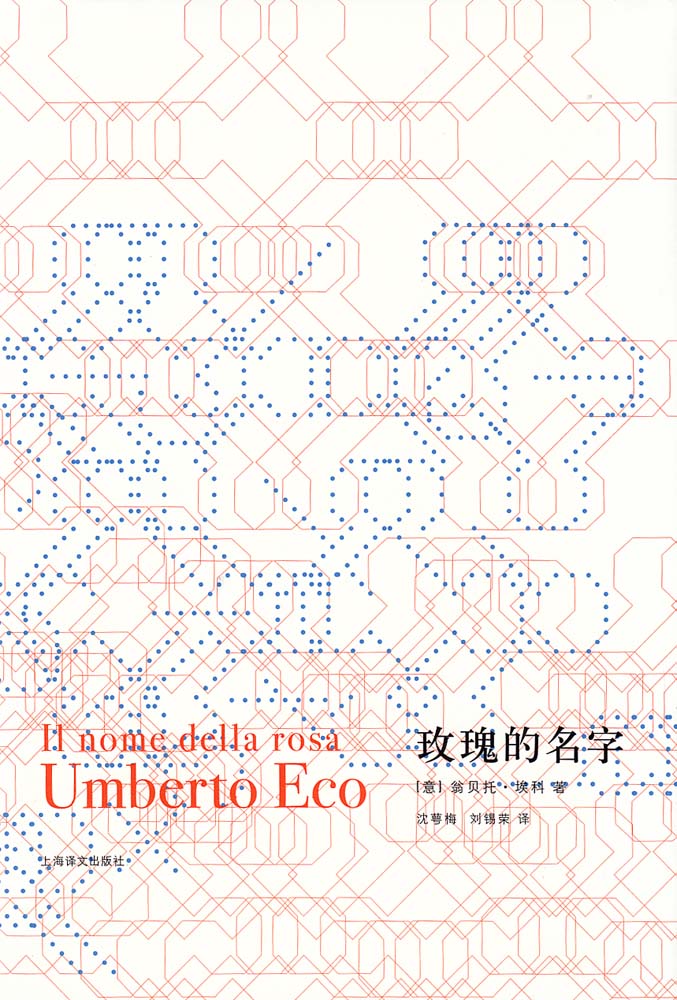 “在一九六五年评论界还没有为博尔赫斯恢复名誉”。在那篇《〈玫瑰的名字〉注释》里,埃科如是说道,这话听起来有点意味深长。实际上早在一九六一年,在与贝克特分享了首届“国际出版人奖”之后,博尔赫斯就已经在国际上名声雀起了。埃科的潜台词似乎是,这种名声至少在当时还没能在纯文学圈内兑现。这有点过于迟钝了。当然他在那篇注释里提到博尔赫斯的目的,却与博尔赫斯的名誉为无关。他也并不想就此去谈论博尔赫斯对他的文学观念有过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实际上他后来对博尔赫斯做出的回应要远比评论来得丰富和有趣。 “在一九六五年评论界还没有为博尔赫斯恢复名誉”。在那篇《〈玫瑰的名字〉注释》里,埃科如是说道,这话听起来有点意味深长。实际上早在一九六一年,在与贝克特分享了首届“国际出版人奖”之后,博尔赫斯就已经在国际上名声雀起了。埃科的潜台词似乎是,这种名声至少在当时还没能在纯文学圈内兑现。这有点过于迟钝了。当然他在那篇注释里提到博尔赫斯的目的,却与博尔赫斯的名誉为无关。他也并不想就此去谈论博尔赫斯对他的文学观念有过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实际上他后来对博尔赫斯做出的回应要远比评论来得丰富和有趣。
十五年后,也就是一九八零年,在这部畅销得让人瞠目的厚达五百多页的杰作《玫瑰的名字》里,埃科营造了一个结构复杂的迷宫式图书馆,除了无数珍本古籍跟镜子以外,还有难解的文字密码机关……围绕着它发生的,是些充满偶然性的离奇死亡事件,还包括迷宫本身最终无法阻止地在那场意外的大火中毁灭。可以想见,任何熟悉博尔赫斯的读者都会对这样的情节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小说出版时,博尔赫斯还健在。要是他老人家听说里面有个狂热执著地守护着那个图书馆的盲修士,也叫豪尔赫(博尔赫斯的名字全称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而且博学多闻、当过很多年的图书馆馆长,他肯定也会对这本书发生浓厚兴趣的。在那篇《〈玫瑰的名字〉注释》里,埃科半玩笑半认真的辩解道:“是建造起来的世界告诉我们故事该如何进展。所有人都会问为什么要用豪尔赫这个名字影射博尔赫斯,为什么博尔赫斯又这样存心不良。我不知道!我需要一个看守图书馆的盲人(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好的叙述想法),而图书馆加上盲人,只能产生博尔赫斯。”
我们姑且先以那种庸俗而又时髦的思维,把埃科对博尔赫斯形象的借用,看作以一种有技术含量的间接表达一下敬意。然后再从更深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一下这种借用背后的意图。对于博学、机智如同那位会探案的威廉修士的埃科来说,借用博尔赫斯的形象创造出一个兼具理性与疯狂的盲修士豪尔赫,其实有三重含义。
首先,声称只为少数人写作的博尔赫斯在六十年代的开始走红,这现象表面上可被看成是现代派的某种余响,而他在写作方式上的创造性发现与贡献,又让人觉得更像是后现代派的一个先声,同时又没有谁像他那样在骨子里更古典。或许在埃科看来,这样的一种状态本身就隐藏着非理性特质,或者说某种疯狂的因素。换句话说,博尔赫斯这位活在现代的古人怎么看都很像个悖论。
其次,这位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太多故事的博尔赫斯,在气息上实在太像个小说里的人物了。因此让“博尔赫斯”亲手引发一场大火并跟那些稀世珍本古籍一起化为灰烬,对于埃科来说实在是个令人兴奋的想法,其本身就很像个关于书和知识占有欲的寓言。埃科就是要以博尔赫斯的方式杀死“博尔赫斯”,以此来表达自己对这位前辈的敬意:博尔赫斯的小说观与叙事方式早在六十年代就启发了他,尤其是那种对偶然性的深刻认识、对侦探小说方式的熟练借用、对书籍和图书馆元素的巧妙运用,对他多年以后完成这部《玫瑰的名字》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当然最终从小说的结构上来说,借用博尔赫斯形象的意义与价值,主要还在于对小说整体逻辑与结构的有效驱动与支撑。可以这样讲,有了盲修士豪尔赫这样的人物和一个迷宫式图书馆之后,这部以十四世纪为背景的小说也就有了核心发条和动力。接下来埃科要做的,就是根据传动原理为它们制造其它的各类辅助配件,精心装入钟表般的小说装置里,处理好所有的接点,然后装上罩在外面的壳子,上紧发条——然后这个发生在七天里的中世纪故事就开始自动运行了。
埃科跟博尔赫斯不同,他不是为少数人写作的。对于他来说,写得精彩好看与拥有广大读者并不矛盾,制造让普通读者寸步难行的精英实验式小说文本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以十九世纪小说才会有的厚度、侦探小说才会有的吸引力、历史钩沉才会有信息量、后现代小说才会有的充满偶然性的游戏意味,同时又对当时正在回潮中的传统的“表现——再现”准则给予鲜明的抵制,这样能写出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这样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种引人入胜的冒险么?雄心勃勃的埃科早就为此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