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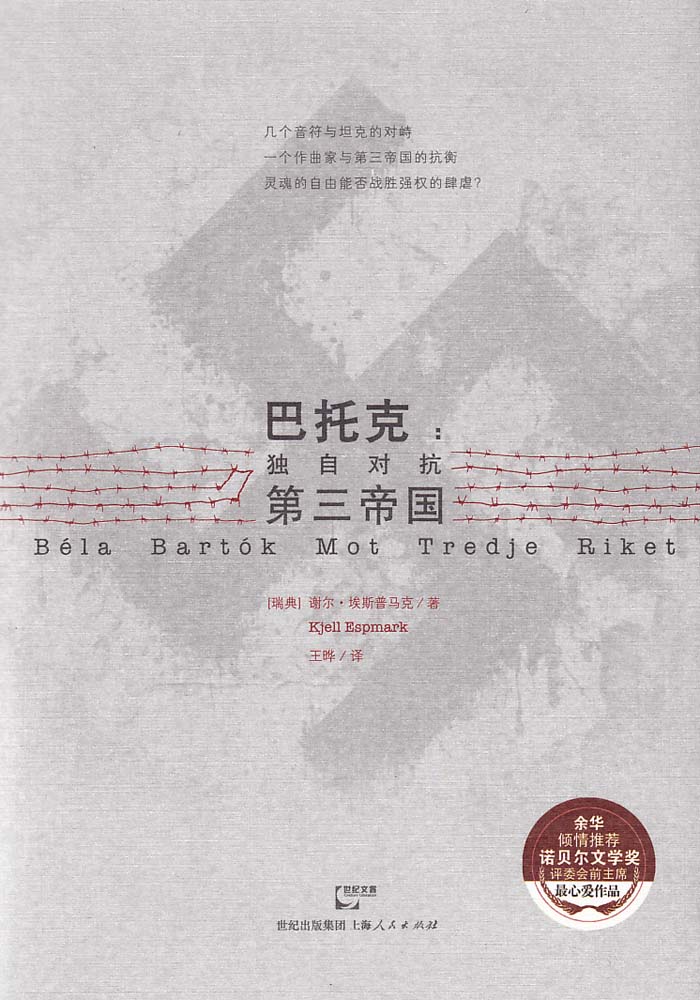 单独的一个人能抵抗强权吗?贝拉? 巴托克 相信可以。和遭受希特勒纳粹政权迫害的犹太艺术家团结在一起,他要求给算作“自愿的犹太人”。他也要求自己的音乐被称为“颓废的”,这是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不可饶恕的挑战。可巴托克坚信他的孤独抵抗里的力量,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在这本书里,我们遇见的是1940年的一天,往美国逃难的途中,在法国南部的巴托克。 单独的一个人能抵抗强权吗?贝拉? 巴托克 相信可以。和遭受希特勒纳粹政权迫害的犹太艺术家团结在一起,他要求给算作“自愿的犹太人”。他也要求自己的音乐被称为“颓废的”,这是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不可饶恕的挑战。可巴托克坚信他的孤独抵抗里的力量,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在这本书里,我们遇见的是1940年的一天,往美国逃难的途中,在法国南部的巴托克。
巴托克也相信音乐是对抗那压倒性强权的真正威胁。“几个四重奏的节拍果真能站在坦克行进的路上吗? ”他问自己。他自答:一个站在官僚和军事控制之外的艺术是构成对强权的明确威胁的自由个体。并且,在音乐中,这孤僻的作曲家跟随了自己的道路,朝向那给他后来的作品烙下特点的简单、明确和空间。
从这本凝练的书里,我读出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双重肖像。从巴托克的图像里,我觉得能看到谢尔·埃斯普马克——我丈夫——加上了从自己的个性和艺术喜好中拉出的重要特征。比如说,他让巴托克有了惊人的听力。这使巴托克在他的录音旅途中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遇见那些农民,感知他们给他的音乐里的精细味道。然后,他为这音乐获得公正的评价而奋斗,“带着爱和尊重”,将其纳入自己的作品。
以同样的方式,谢尔接近了那些他在自己作品中描绘的人物。个人的特写镜头是他大量作品中的关键线条。贝拉·巴托克和谢尔的系列小说《失忆》中的七个主人公在一起。同样也和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那些出现在谢尔的《黑银河》或《狼时间》里的人物在一起。巴托克的肖像基于详尽的资料而塑造。却因为对音乐家思想和情感的侦听而有了生命和深度。这肖像打上了谢尔对自己热爱的音乐的作曲家的同情的印记。
我也以为,巴托克对权力的“无意义的抽象”的批评——那剥夺人的个性的——和谢尔有时对当下瑞典官僚主义者的批评有关。当个人的命运和私人的灾难减化为权力设备可操作的符号和数字时会发生什么呢? 巴托克在书的最后对自己的审讯,我当然能认出来!“他对他的生命作了些什么?”他问他自己。以同样的方式,谢尔在两本新近的作品中审视了自己的潜在动机,《记忆说谎》及《狼时间》。在那里,他拨开了所有的浮渣——那遮盖了最下面的真实的——一个简单的木板,最终可以站立。
同样地,我也看到,巴托克追求的形式的严格也对应着谢尔自己的风格理念。他的小说从来都不长。故事集中于那最精华的。多余的字眼和短语全部削去。这让文字绷紧,有时这是费力的。同时,多读上几回,每读一回,都能获得新发现。
也许秘密就在于,那宽大和包容的想像力打开了存在而未想到的生活层面——巴托克是,谢尔·埃斯普马克也是。在这本书里有一个作家自己体验的,却让巴托克接管的一个清晰的印象。一次他睡在一间古老的农舍。入夜,他的屋子里闹起鬼来。充满了各种声音:哀号、唠叨、窃笑、警告和争吵。他发现,声音来自壁炉里薄薄的风门。主人拒绝了他理性的解释。自然,他得到了个教训。也许那风门,是帮助死去的和幸存者找到联系的装置。他自己不就是让逝去的站在我们面前的工具吗?
谢尔·埃斯普马克的生活和写作的座右铭是“largesse”——一个法语表达,指对不同的性、民族、社会阶级和年龄的广泛慷慨。在贝拉?巴托克的肖像中,他让作曲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征服势力的语言是区别,他的是桥梁、兄弟情、感性的直观性。”
Monica Lauritzen
莫尼卡·劳瑞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