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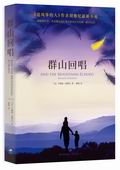 动荡的中东地区自古就是世界的“火药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是饱受战乱之苦,田园荒芜不说,好端端的家毁于战乱,亲人四处分散此生不能相见。在战争的催生之下,集体的“受害者”心态应运而生。其后,这种心态被移植在文学里,成就了一系列以苦难、离散为主题的“伤痕文学”。比如,西敏·达内希瓦尔在《萨巫颂》里描写的上世纪40年代的伊朗贵族,抑或是萨义德·卡书亚的《耶路撒冷异乡人》里那些个骄傲而又自卑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他们在各自的世界里兜兜转转,转眼又以相似的模样出现在卡勒德·胡赛尼的笔下。 动荡的中东地区自古就是世界的“火药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是饱受战乱之苦,田园荒芜不说,好端端的家毁于战乱,亲人四处分散此生不能相见。在战争的催生之下,集体的“受害者”心态应运而生。其后,这种心态被移植在文学里,成就了一系列以苦难、离散为主题的“伤痕文学”。比如,西敏·达内希瓦尔在《萨巫颂》里描写的上世纪40年代的伊朗贵族,抑或是萨义德·卡书亚的《耶路撒冷异乡人》里那些个骄傲而又自卑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他们在各自的世界里兜兜转转,转眼又以相似的模样出现在卡勒德·胡赛尼的笔下。
小说《群山回唱》以一个颇为辛酸的故事作为开场:穷山沟里来了魔王,要抓走几个可怜的童男童女,一村子人愁眉不展,如临大敌。这是阿卜杜拉的父亲在卖掉女儿帕丽之前讲给儿女听的故事。帕丽最终还是被卖掉了。我们当然不能责怪父亲的无情。乱世之中人如蝼蚁,家被毁了,生活无法维系。为了活下去,就算是违心的,也只能咬着牙坚持下去,因为只有“砍掉一根指头,才能把手保住”。
作者胡赛尼显然比阿卜杜拉幸运得多。出于家庭的缘故,他早早地离开了处于混乱之中的阿富汗。他离开的时间恰到好处,太早不会留下太多记忆(就像帕丽),太晚就会过于沉溺往事不可自拔(就像阿卜杜拉)。胡赛尼身兼移民作家与医生的双重身份,医生以手中之刀治病救人,作家的职责则是真实客观地反映事实真相,“以正义和公平的原则负责任地描写阿富汗”。在这两种身份之外,胡赛尼也是个普通人。他自称不是阿富汗问题专家,因而,无意也无法提出济世救人的良方。较之国际大势,胡赛尼更为关心普通人的生存状况。他的笔下仿佛上演着现代版的一千零一夜。《群山回唱》里讲了不止一个故事:阿卜杜拉的故事、舅舅纳比的故事、继母帕尔瓦娜的故事,甚至是义工的故事。胡赛尼的故事没有绮丽的异国风情,也不以复杂、奇诡的剧情取胜,更与宏观大局无关,打动人心的是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真情实感。
小说涵盖了大半个世纪,从二战后的四十年代讲起,直到当下,以一个家庭几十年间的变迁书写苦难中的家国民族。胡赛尼说:“这个国家遭受的苦难,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记载,它们远比我的笔墨更有见识,更有说服力。”他无意在苦难深重的同胞伤口上撒盐。事实上,《群山回唱》不像《追风筝的人》,并没有对那些黑暗日子的直接描写。尽管如此,“苦难”仍是小说唯一的关键词。阿富汗有多少战乱,胡赛尼笔下就有多少离难。阿卜杜拉失去了妹妹,帕丽离开了亲人,弟弟伊克巴尔一家有家难回,被当作难民收容。这样的战争孤儿、这样的离散故事在今天的阿富汗不是少数,几乎随处可见。不过,这种苦难并不仅仅限于阿富汗,而是跟随主角们流亡的足迹被散播到天涯:从阿富汗的荒漠到爱琴海的小岛,再到法国巴黎,甚至是美国加州,故事到了哪里,战争(暴力)的阴影就跟到哪里。悲伤是烙在脸上的“胎记”,将他们从人群里分离开来,并将伴随他们的一生。
作为现实的写作范本,《群山回唱》里自然也不乏对混乱现状的反思与抨击。胡赛尼对战乱之后的阿富汗应该不抱有盲目的乐观,他见证了战后的种种乱象,并反复表达出他的忧虑。几十年间,战火连绵,苏联人、军阀、塔利班、美国人,各种势力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带给阿富汗的不是充满希望的田野,而是一轮又一轮永无休止的战争。停战后,战争的后遗症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处于“后战争时代”的喀布尔照旧有无谓的施暴。人们为了利益相互争斗,甚至将自相残杀的刀锋对准无辜儿童,“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胡赛尼言词犀利,语带讽刺。战前移民外国的年青一代纷纷在战后回归,这种回归纯粹是经济利益的需求,并无任何情感上的认同。他们在阿富汗度过的童年实在太遥远,“仿佛一份遗物”;对于发生在身边的苦难,更是无动于衷,更像是“观光客在看表演”。
从《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到《群山回唱》,回荡在胡赛尼小说里的主旋律不是激动人心的进行曲,而是一曲曲民族家国的悲歌。他写的是爱,讲的是情,唱出的是命运。《群山回唱》一开始,卡勒德·胡赛尼就借魔王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他用良善去抚触那些生命,给那些陷于悲苦的人们带去幸福”。这应该是他写作的终极目的。虽然小说不能改变世界,也未必能给人“幸福”,但它可以是慰藉,是希望。只要能给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的行路人带来光亮,哪怕只是一点点,对胡赛尼来说,也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