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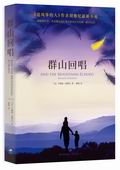 继《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之后,生于阿富汗的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携新作《群山回唱》再次引发读者关注,被美国亚马逊书店评选为2013年上半年最佳图书。 继《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之后,生于阿富汗的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携新作《群山回唱》再次引发读者关注,被美国亚马逊书店评选为2013年上半年最佳图书。
这部小说有着胡赛尼一贯小说中的母题: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往事对现实的纠缠,并以同样的兴味描绘出两个世界之间的中间地带,一个是异彩纷呈的寓言的世界,另一个是更模糊,也更为阴暗的现世。不过相比以往的作品,这部小说更令人信服与扣人心弦。
1952年,阿富汗,贫穷的村庄沙德巴格。10岁的男孩阿卜杜拉和3岁的妹妹帕丽经历了一场可能永生难以挽回的骨肉分离。他们的妈妈在生帕丽的时候死于大出血,父亲萨布尔是个卖苦力的老实人,勉强支撑着艰难度日。他无力拉扯两个年幼的孩子,又给孩子们娶了个继母帕尔瓦娜。帕尔瓦娜的哥哥纳比在喀布尔一户富裕人家里做厨子兼司机,瓦赫达提夫妇看似平淡的生活被打破,女主人妮拉一直无法生育。纳比舅舅居间牵线,帕丽被卖给了妮拉,开始了新生活。这就是卡勒德·胡赛尼在《群山回响》中所讲述的故事。继《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之后,再一次执笔的他,描绘出阿富汗跨越六十年、三代人的历史,每一个人物的生活合奏出一部复调的哀歌。
胡赛尼在《群山回唱》构架的宏大叙事中一反之前的常态,弱化了战争场景,但却未削减阿富汗民族的变迁在人们心中烙下的伤痛。“在有些夜晚,他会梦见自己又一次置身荒漠,一个人,四下都是山,只有一点点细小的微光在远处闪烁,明明灭灭,如同一句暗语。”胡赛尼借阿卜杜拉的遐想契合隐匿的主题,群山回唱出的到底是何样的曲调?胡赛尼将家族的变迁裂变细化到每一个人物的转折之中,在神话寓言的讲述中折射出命运的拐点。小说以魔幻故事开场,魔王给父亲萨布尔一次残酷的爱的考验,将父爱和生存放在天平上,衡量着二者的偏离。女儿帕丽牵扯着父亲与儿子阿卜杜拉之间的距离,自从父亲和阿卜杜拉把帕丽卖给瓦赫达提夫妇从喀布尔回来,一个故事也没讲过,阿卜杜拉觉得父亲大概把自己的灵感也一并卖给了他们,仿佛在一个富有神性的国度,休想做违心的事情,否则会得到惩罚。
在电影《我与狗狗的十个约定》中,罹患重病的母亲曾在临终前交给女儿一只狗,并告诉她,要善待狗狗,因为他就像妈妈一样陪伴在她左右。动物的灵性延续到沙德巴格中的大狗舒贾身上,他见人就躲,只有帕丽是个例外,他对帕丽的爱是浩瀚而不加掩饰的,而在帕丽走后,村里没有一个人问过帕丽,甚至没人提起过她的名字,阿卜杜拉吃惊,她竟然从大家的生活中消失得如此干净,只有在舒贾身上,阿卜杜拉能看到自己的悲伤,一种移情的哀痛。阿卜杜拉能看见一张张脸,藏在大地上隆起的群山中,带着狞笑,邪恶地俯视着他和帕丽,这是群山给予他们离别的来自大自然的讯息。
帕丽早逝的母亲曾唱过一首摇篮曲:“我瞅见伤心的小仙女,待在纸树影子下。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晚风把她吹走了。”父亲为了生计,砍掉了那棵橡树——它高出沙德巴格的一切,也是村里最老的老寿星,它有一个传说:如果你想许愿,就跪在树下,瞧瞧把愿望告诉它,如果树答应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它就会在你头顶落下树叶,不多不少,正好十片。帕尔瓦娜、马苏玛、萨布尔倚着庞大的它荡秋千,接着是他们的后辈人……它不仅仅是一棵树,它俯瞰着一代代人,无形中保佑着他们不受战争与饥饿的冲击,它的倒下如蝴蝶效应一般引发了生命的失控和性情的逆转:萨布尔至死仍逃不过劳作的折磨,拿着割甜菜的镰刀,满手的水泡,血流不止;马苏玛从树上跌落后瘫痪不起;一度让母亲陷入史诗般痛苦的女暴君帕尔瓦娜却沦落到日复一日喂鸡、劈柴、从井里提水的家庭琐事之中,她一直的缄默,是在保守着只有她和群山才知道的秘密,原本一切属于马苏玛艳羡的目光没有因为她的不在场而转移,妒忌之火让她承载了双重的重任,得到了萨布尔,无奈的供养着马苏玛,每况愈下的生活寡然无味。
有的人沉寂的留下,也有的人匆匆离去,帕丽的舅舅纳比就把离开沙德巴格看作一场逃亡。阿富汗人热爱诗歌,就算最没文化的人,也背得出哈菲兹、海亚姆或萨迪的诗篇。妮拉如同一个与主流相斥的异类:作为诗人,她违背传统,从不遵循格律,她写肉体上的爱,写情人们枕边私语;作为妻子,她不拘小节,放浪形骸,甚至在丈夫重病时携养女离开;作为母亲,她试图用对帕丽的爱抹去过往的情殇和不羁。直到那一幅幅描摹的轮廓映入眼帘,瓦赫达提先生与纳比的同性之爱刺痛了她的灼伤的神经,而纳比也从未获得过开口说爱的机会,更无法表达对妮拉秘密且热烈的爱恋,自由不过是错觉,因为最想做的事已经不复存在了。
庆幸的是,帕丽和阿卜杜拉在几十年后再度重逢,亲人的感应强力地吸附着地球的引力,从喀布尔到巴黎,每个角落,每个暗处,每条裂缝,都隐藏着鲜活的记忆。它们在分分秒秒促成一桩桩离别和重逢,让人在往昔的底色上体味失而复得的幸福,在瑟瑟山风中重听夜鸟啁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