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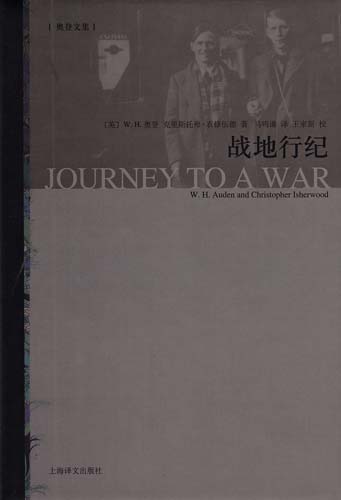 《战地行纪》的散文部分从奥登和衣修伍德1938年1月28日进入广州开始,一直写到1938年6月12日他们乘坐“亚洲皇后”号邮轮离开上海为止,当时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激战正酣,两位年轻的英国作家几乎穿梭了大半个中国,因为中国当时正在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他们在中国所受到的礼遇也就可以想象了。在国民政府方面,他们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熊式辉、蒋鼎文的接见,而在汉口史沫特莱的居所,他们也偶遇了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博古。所有这些人物,对于中国当代读者而言都堪称传奇人物,当然对于热爱西方诗歌的我来说,奥登也是一个传奇人物。这样的交集本身就令人神往,那个英文版《奥登诗选》封面上满脸皱纹的脸庞(奥登晚年照片),竟然也年轻过,更让人惊讶的是,奥登竟然和一众中国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为他们拍照(奥登为周恩来拍的那张照片,是我见过的周恩来最漂亮的照片),向他们提问,倾听他们的回答。 《战地行纪》的散文部分从奥登和衣修伍德1938年1月28日进入广州开始,一直写到1938年6月12日他们乘坐“亚洲皇后”号邮轮离开上海为止,当时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激战正酣,两位年轻的英国作家几乎穿梭了大半个中国,因为中国当时正在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他们在中国所受到的礼遇也就可以想象了。在国民政府方面,他们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熊式辉、蒋鼎文的接见,而在汉口史沫特莱的居所,他们也偶遇了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博古。所有这些人物,对于中国当代读者而言都堪称传奇人物,当然对于热爱西方诗歌的我来说,奥登也是一个传奇人物。这样的交集本身就令人神往,那个英文版《奥登诗选》封面上满脸皱纹的脸庞(奥登晚年照片),竟然也年轻过,更让人惊讶的是,奥登竟然和一众中国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为他们拍照(奥登为周恩来拍的那张照片,是我见过的周恩来最漂亮的照片),向他们提问,倾听他们的回答。
从另一方面,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也因为奥登和衣修伍德细致的描述而变得生动起来,这是宋美龄:“她是个小个子的圆脸女士,着装高雅,与其说是漂亮不如说是很活泼,拥有一种几近可怕的魅力和自信。”这是蒋介石:“我们几乎不可能从眼前这个谢顶的、面目和善、眼睛黑亮的男子,认出新闻短片里那个披着斗篷、腰板挺得笔直的人物。在公开和正式的场合,蒋近乎是个阴险的怪物;他犹如某种幽灵虚弱而面无表情。在这里的私人场合,他显得和蔼而腼腆。”这是博古:“博古对每件事情都会笑——日本人,战争,胜利,失败。我们问他八路军都有什么最新消息,眼下的状况如何?‘很可怕!’博古哈哈笑着。”
这样的细节足以引起中国当代读者猎奇式的兴趣,当然作为文学家出身的“业余记者”,——奥登就曾说过:“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们的视野比一般的新闻记者要广阔得多。仅举一例:当奥登和衣修伍德“从严酷的旅行中解脱出来”,在温州登上海轮准备前往上海,他们倚着栏杆,把硬币和十美分纸币丢到码头边沿,然后等着,看它们多久才会被人注意到捡起来。“一枚硬币就落在一个小男孩旁边,也就四或五岁,身上很脏。”然后小男孩不动声色地用脚趾头去够那个硬币,非常缓慢地把它拨到伸手能捡的位置,眼睛甚至都不曾往下看。把它放进口袋后,他站起身,带有一种极其漫不经心的神气,一摇一摆走开了。跟着则是英国小说家的慨叹:“这是我平生所见最令人震撼的事情之一,它道出了苦力挣扎求生的真实一幕。”如果这样的细节都被充分注意,可以想象这会是怎样一部巨细靡遗的珍贵历史记录。1938年战乱中的苦难中国借由这些文字而被完整保存。半年多的观察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能算是惊鸿一瞥,但是文字自有一种切入意义深层的奇特惯性,换句话说,这本书仍旧可以使我们对于历史产生一种崭新的认识,甚至像刚打开的蒸笼,飘着触手可及的香味。
1938年,组诗《在战争时期》和长篇的《诗体解说词》告竣。这些诗作很快被誉为“三十年代奥登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许是三十年代最伟大的英语诗歌”。
如果《战地行纪》只有散文部分,它仍然会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但是在一众关于中国现代史的目击式见证式的书籍中,它顶多也就是较有特色的一本罢了。使这本书格外显得与众不同的是,奥登根据此次中国之行创作的组诗《在战争时期》以及长篇的《诗体解说词》,这些诗作提升了本书的价值,使它超越了新闻报道火热又急躁的面目,获得了某种恒久的文学价值。这些诗作带领我们上升,历史画卷——哪怕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终于在视野中变得渺小和缥缈起来,从而获得了某种寓意,成为某种象征,而人在历史面前忐忑不安的道德动机则成为首先需要探讨的紧迫问题。
《战地行纪》散文部分最终是由衣修伍德操刀的,因而时常可以见到对于奥登的描述,比如“奥登递过了雪茄”,“奥登在看《荒凉山庄》”等等,但是衣修伍德的创作全部取材于他和奥登分别撰写的旅行日记,也就是说,奥登将中国战地行的事实报道部分都让给了衣修伍德来做。中国之行两个月后,组诗《在战争时期》和长篇的《诗体解说词》告竣。这些诗作很快被誉为“三十年代奥登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许是三十年代最伟大的英语诗歌”。(语出奥登研究者门德尔松),而约翰·富勒则将这些诗称作“奥登的《人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