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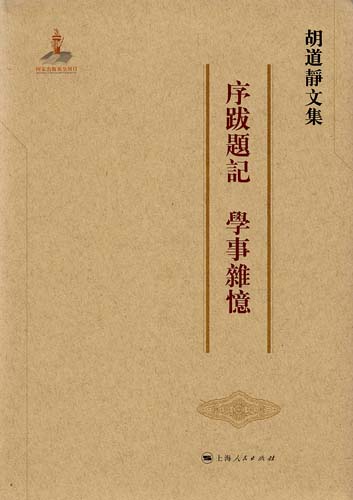 今年是胡道静先生(1913-2013)诞辰百年的日子,上海人民出版社此前已出版了《胡道静文集》,以示纪念。胡先生的学术研究生涯,贡献至伟,可以概括为《梦溪笔谈》的校证之功、古籍整理的导引之功、科技史论的创新之功、文化史志的开拓之功、人才队伍的培养之功。 今年是胡道静先生(1913-2013)诞辰百年的日子,上海人民出版社此前已出版了《胡道静文集》,以示纪念。胡先生的学术研究生涯,贡献至伟,可以概括为《梦溪笔谈》的校证之功、古籍整理的导引之功、科技史论的创新之功、文化史志的开拓之功、人才队伍的培养之功。
“活体书联网”
如今互联网的发展,使书书相联,书人相联。但在互联网发明之前,胡先生对于目录学和文献学的博学与专精,几可用“活体书联网”来形容。胡先生自幼从其父胡环琛(1886-1938)和伯父胡朴安(1879-1974)学习文献目录之学,受到了严格和良好的历史文献学的训练。手抄、摘录、校注等是胡先生一辈历史文献学家共同的学术研究方法,所谓“手抄一遍,胜读十遍”,从而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逐步积累构建起了历史文献的“活体书联网”。胡先生在1982年所写的《谈古籍的普查和情报》一文,充分体现了胡先生在学术情报方面的积累和应用目录学方法的应用。金良年、孔毅同学与我自1982年大学毕业之后,共同考上了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分别师从顾廷龙先生(1904-1998)、潘景郑先生(1907-2003)和胡先生问学。读书期间,胡先生给我们上“应用目录学”的课程,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到宋代陈振孙的 《直斋书录解题》和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特别是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以及《四库简明目录》和众多的标注,胡先生将目录之学的前后流变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古典目录中的大小类目提要和各种文献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种古籍的书名目录、版本卷次演变等都一一详述,可谓融会贯通,烂熟于胸中,头脑中存储着一幅内容极为丰富的文献互联网络图,令人叹服。胡先生在讲课中特别强调目录学的应用性,即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快速准确地查找到所需要的主题文献,要求我们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注意进行各种书籍的目录、版本的标注和比勘,要掌握查找古籍文献的“雷达”,做到脑有成竹,这是目录学研究的基本功。其中“互著别裁”就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反映出文献学的学科与主题的交叉性特征。胡先生长期在出版社主持编辑工作,经常要通过目录版本的考证与校勘来进行出版选题的确定,同时需要回应学术界的相关学术咨询,这些都使胡先生在长年的工作中形成了应用目录学的研究方法,使其在历史文献的大海中游走自如。由于胡先生具有独到的辨别路径的方法,很多学者都喜欢向胡先生请教,而胡先生也总能给予满意的回答。顾廷龙先生曾经讲过:“治学而不习目录版本之业犹访胜境而徘徊于门墙之外也。”胡先生注重目录版本之学的基础训练与应用,这对于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而言,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具有世界眼光和影响的跨界大师
胡先生以研究古代科技史和古典文献学著称于世,但同时胡先生又具有学术研究的世界视野,学贯中西,这一点难能可贵。胡先生家中曾挂有一副对联:“踏开世界不平路,援登科学第一峰。”尽管这副对联为姜亮夫先生(1902-1995)所书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胡先生面向世界的学术研究胸怀与崇高的学术追求境界。记得1979年,胡先生在《书林》第2期发表了《世界上现存最早印刷品的新发见》一文,让多年来处于对外封闭状态的中国大陆学界能够了解到书史研究的最新国外动态。胡先生的学术成就特别是《梦溪笔谈校证》的学术贡献令学界赞叹,其学术影响力远播海外,胡先生也由此与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1900-1995)结下了数十年的友谊。1981年,胡先生被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选为通讯院士。
胡先生是一位学术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的跨界大师。从七卷本的《胡道静文集》可以了解胡先生研究领域所涉略的范围:卷一为“上海历史研究”,卷二为“农史论集·古农书辑录”,卷三为“梦溪笔谈校证”,卷四为“新校证梦溪笔谈·梦溪笔谈补证稿”,卷五为“沈括研究·科技史论”,卷六为“古籍整理研究”,卷七为“序跋题记·学事杂忆”。胡先生自己也曾于1983年将其著述分为五类:“古籍工作”、“沈括研究”、“科技史论”、“图书馆志”、“海隅笔丛”。据此可见胡先生研究的范围包括了古今中外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相关领域,可谓是跨界大师。诚如胡先生自己所述,以体育运动比喻,他所从事的是全能运动。
“平凡中蕴含着杰出,静默中闪现出火热”
胡先生的长子胡小静曾用两句话来描述其父亲的生命特点:“平凡中蕴含着杰出,静默中闪现出火热”。这正是胡先生学术研究与待人处事的生动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