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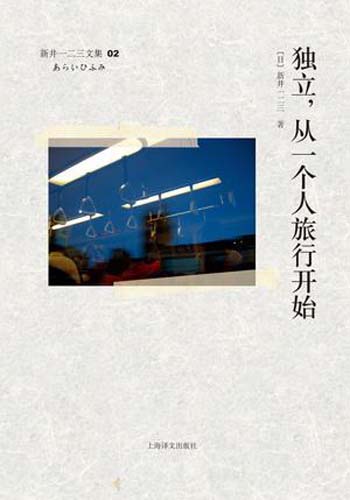 最初会阅读新井一二三的《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纯粹是被书名所吸引去的:独立、一个人、旅行,这些字眼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 最初会阅读新井一二三的《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纯粹是被书名所吸引去的:独立、一个人、旅行,这些字眼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
我从小就最爱捧着地图册,从中国翻到世界,百看不厌。那一个个陌生的地名,令我神往。小小的我梦想长大后学李四光成为地质学家,因为我以为,只有地质学家可以走遍那些出现在地图册上的任何地方。
阅读《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的过程中,首先找到的是共鸣感。共鸣,是读书的一大乐趣:读者与作者之间,无形中建立了一种默契,你知我知,尽在字里行间。作者在序的开头就说:“曾经很多年,我花费最多的项目是飞机票。对于其他女孩子着迷的名牌服装、化妆品等,倒一概沾不上边儿。”而我则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将一句网络流行语“给自己一个LV,不如给自己一个long vacation”作为座右铭用在QQ签名上。
作者十四岁就有了第一次单独踏上旅途的经历。从二十岁开始,作者从日本启程向世界飞跃,走遍中国,定居北美,漫步中欧,走向古巴、留恋越南,并在三十三岁“厄年”之际调转方向,开始过上恋爱的两人生活。我与作者的经历恰恰相反:二十岁以前除了学校的春秋游,几乎没有旅行过。自从踏上工作、有了自立的经济之后,我每年都计划大小不等的旅行。
我的初次单身旅行,选择的目的地是多彩贵州,因为那里地处云贵高原,有我从小就向往亲临的黄果树大瀑布,有充满神秘色彩的诸多少数民族,与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上海完全不同。初次一个人旅行,在《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 有一段话完全能表达我的感受:“经过第一次的独立旅行,我似乎获得了另一个身份似的,是不同于平时的我,家人、同学们都不认识的另一个自己。”
引起共鸣的,还在于作者对美食的爱好:“关于旅游的很多记忆,随着时间已消逝,但是在旅途上吃到的一些美味,过了二十年都念念不忘。”作者笔下的中国大西北面条之路,加拿大的“中国派”,维也纳的巧克力蛋糕,古巴的兰姆酒,澳门的菠萝白,东京的萤乌贼、荞麦面,在台湾吃到的上海小笼包,世界各地的美食美酒仿佛摆成了一桌盛宴,令人直冒馋虫。我一向认为,旅途中品尝到的异地美食,决定了旅行的质量:吃得好才能玩得好,美食是了解当地人文特点的捷径。每次旅行归来,我一定不忘整理美食照片,记录美食笔记,那些旅途中品尝到的美味,在舌尖上打转儿,回味无穷。
作者笔下旅行途中遇到的不同文化中的各色人等,亦令人惊叹。上海偷渡客阿德用蓝色钢笔写的信,内容的真诚打动了作者的心;北京的摇滚乐团“不倒翁”,其中有几人后来成为了中国耳熟能详的大明星; 加拿大的嬉皮夫妻靠政府养育两个孩子,却自制水果风干箱开车横越加拿大;不爱旅行也不想结婚的斯洛伐克移民,住在风景般的湖景房中每周六翻阅报纸上的征友启事寻找女伴; 古巴飞机上英俊的空少边跳舞边推荐兰姆酒,充满了拉丁民族的热情;越南的“西贡小姐”现象令作者陷入了道德的困惑中……异地的风光令人赞叹,融入了异地文化特性的人物更是鲜活的风景,无可复制。
读书的另一大乐趣,在于找茬。找茬会让读者感觉到自己的优越性,带来满足感:虽然作者是成功人士,出版了书籍,但居然被我找到错误,是不是我有比作者的过人之处呢?我为此书找的第一个茬:作者的文笔实在不敢恭维,文中描写风景、美食的词汇都很有限,诸如朴素、可爱,重复率也很高。起初我怀疑翻译者水平,仔细查找封面扉页才发现,竟然是日本的作者直接用中文写作的。而且随着阅读的深入,体味到作者在简单文字中所透出的自由、随性、惬意与丰实。
第一个茬没找成功,我开始找第二个茬:书名叫《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但此书最后却用逾四分之一的篇幅来描述情侣、亲子乃至三代同堂游,并没有将独立宣言贯彻到底。或许这是东方文化下女性难以摆脱的限囿——女人的最佳归宿始终是家庭。又或许,作者想表达的是,在一个人旅行的过程中,建立起了坚强的独立人格,而这种独立人格的最终体现,强调的并是“一个人”,而是找到属于个人的“幸福”。
第二个茬不能确定,我又找到了第三个:作者在“十四岁的初次旅行”一节中,曾提到“我想做的事情,只要不给父母带来太多麻烦,他们是不会加以阻止的”。而在近结尾的“母语世界”中,却将自己十二年之久旅居国外的原因主要归咎于母亲这个蛮横的导演:“她是很蛮横的导演,命令你去演她所指定的角色……”原来作者的“独立”是相对于她的母亲而言的,当她强大到能摆脱母亲时,“有了这么点距离(离娘家坐车四十分钟)、十二年的时间、加上能锁住的铁门和丈夫的保护,我才有了信心能够经营独立的生活”。也许是文化差异吧,我无法理解一个女儿对母亲会产生这样强烈的摆脱心态。
阅读《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我一直在思索:人为什么要旅行?是为了逃避现实?还是更好地面对自己?书中或许有答案,又或许没有;即使有,也是作者的答案,不一定是读者想要的——思与辩,我想这就是读书的最大乐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