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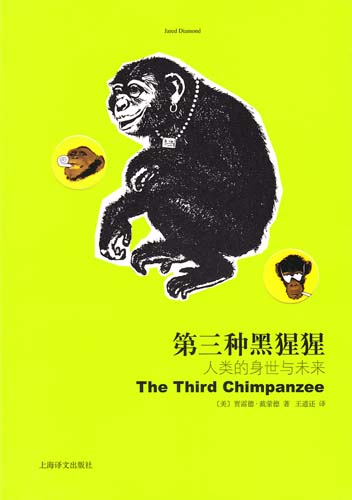 今年7月,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发表了一次讲话,提到他读过的两本书:一本是贾雷德·戴蒙德的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一本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戴维·S. 兰德斯的《国富国穷》。这两本书都试图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和地区强盛富裕,有的则贫穷落后。前者强调地理因素,后者则强调文化,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影响。罗姆尼的讲话基本上是说,靠得这么近,以色列的人均GDP是两万一千美元,而巴勒斯坦只有一万美元,所以地理因素——什么有没有铁矿石之类——不是关键,文化决定了这一切。 今年7月,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发表了一次讲话,提到他读过的两本书:一本是贾雷德·戴蒙德的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一本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戴维·S. 兰德斯的《国富国穷》。这两本书都试图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和地区强盛富裕,有的则贫穷落后。前者强调地理因素,后者则强调文化,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影响。罗姆尼的讲话基本上是说,靠得这么近,以色列的人均GDP是两万一千美元,而巴勒斯坦只有一万美元,所以地理因素——什么有没有铁矿石之类——不是关键,文化决定了这一切。
罗姆尼因为满嘴跑火车丢分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他的话一般不能当真。如果较真的话,正如《波士顿环球报》所指出的,以色列的人均GDP其实是三万一千美元,巴勒斯坦是一万五千美元。而且考虑到巴勒斯坦这么多年局势不稳,它经济发展得差些,肯定不能全怪文化。不过如果我们把“对国家富强来说,地理因素重要还是文化和制度因素重要”这个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考虑,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戴蒙德因为自己的书被共和党的人给否定而气愤不已,干脆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反驳。戴蒙德说,我的书的确强调地理因素,但我从来没说过什么铁矿石的重要性,我说的是生物特性和交通条件。就算是那本强调文化差别的书,也没有忽略地理因素的影响,这两种解释并不是互相独立的。
在我看来,戴蒙德的反驳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如果你像中学生的政治考题那样,对国家强盛靠什么的回答是列出一二三各种因素都有作用都重要,那你应该干脆把所有这些因素都写在同一本书里,专门强调一头的答案怎么能得高分呢?其实,这两本书之所以给出不同的答案,根本原因是它们看问题的尺度不同。《枪炮、病菌与钢铁》用的是特别大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描写整个大陆在千年乃至万年的历史中的命运,比如非洲为什么比欧洲落后。而《国富国穷》的尺度则要小得多,谈论比如英国在工业革命中的作为。
尺度,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物理学研究非常讲究尺度。计算汽车和火车的运动只要把地球当成平面就可以了,布置国际航线则必须考虑地球的球形形状,而研究行星运动又可以把太阳都当成没有体积的质点。尺度思维的一个要点在于,当你考虑大尺度问题的时候,小尺度的现象常常可以忽略或者简化。统计力学不跟踪单个分子的个别运动;在等离子体物理学中,如果你研究的是离子尺度的现象,那么因为电子质量小得多,它们的运动就可以用某种流体代替。而更重要的是,从小尺度现象出发往往解释不了大尺度问题。正如《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我们从《史记》这种史书中悟出来的道理,并不适合研究大国在百年以上时空的兴亡。
黄仁宇写《中国大历史》一上来先谈“十五英寸等雨线”,这个思维与“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戏剧性开头完全不同,他讲出来的故事也绝对不会用到《明朝那些事儿》中的桥段。研究大尺度问题,必须关注一些长期不变的因素,也就是“硬条件”。一位皇帝的雄心和几名将领的智勇也许可以在小尺度内左右一个中原王朝的命运,但是改变不了华夷相争这个大局面,因为后者是由这个硬条件所决定的:因为雨量充沛,华夏物产丰饶。在《中国大历史》中,这条十五英寸等雨线注定了中国农民在两千年内不得不跟塞外牧人斗争的宿命,而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一个大洲在上万年内的运数,竟取决于这个大洲有多少可供人类驯化的动植物。有些硬条件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种种限制,使人们不能恣意而为,而有些硬条件则又是我们的重大机遇。正因为有了这些限制和机遇,历史的演化才成了带着镣铐跳舞,反而不平淡了。
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放大到百万年,把空间尺度放大到整个人类,这个故事和道理又将是怎样的呢?这就是戴蒙德二十年前写的《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此书、前面提及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和《崩溃》,都出自这位UCLA地理学教授之手,而由于在逻辑上后两本的内容其实已经包括在第一本中,《第三种猩猩》可以说是代表了戴蒙德对人类社会的根本看法。罗姆尼可以胡乱评论以色列为什么比巴勒斯坦发达,而这本书则能告诉我们人类为什么比动物发达。但这个看法可能跟任何一位传统历史学家的看法都不一样,因为戴蒙德并不是历史学家。他是一个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