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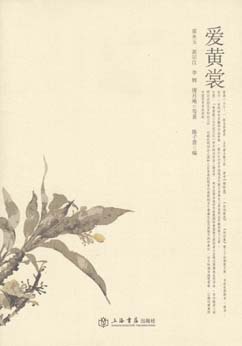 昨天是散文大家、藏书家黄裳先生辞世后的“五七”之日,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主办,上海图书公司承办的黄裳先生追思会昨天在上海古籍书店举行。黄裳先生生前故交、同事、晚辈以及他的读者到会追忆这位逝去的文化老人。 昨天是散文大家、藏书家黄裳先生辞世后的“五七”之日,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主办,上海图书公司承办的黄裳先生追思会昨天在上海古籍书店举行。黄裳先生生前故交、同事、晚辈以及他的读者到会追忆这位逝去的文化老人。
他把“花边”做成出彩文章
出席追思会的有85岁高龄的翻译家姚以恩,黄裳先生的女儿容仪,黄裳在文汇报的同事、老记者、传记文学作家郑重,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子善,篆刻家茅子良以及专程从北京、西安、嘉兴、安徽等各地赶来的黄裳先生的读者,在画像中黄裳微笑的“注视”下,他们回忆了与黄裳先生交往的点滴过往,并解读了黄裳先生作品的现实意义。
郑重是黄裳先生在文汇报的同事。郑重说,自己跟黄裳先生年龄相差很大,他进文汇报时,黄裳已经在“文革”中“落难”,交往不多。他尤其记得刚进报社时看到黄裳先生坐在角落里编稿子,后辈们对他都很尊重,遇到业务难题,还要找黄裳帮忙。“他在取新闻标题方面有点石成金的本领。”“文革”时,黄裳被送到报社的车间劳动去了。“黄裳虽然文章写得好,但是收报纸就显得有点笨手笨脚了。”郑重说。
“作为一名记者,黄裳先生有独特的眼光,在别人看着是‘花边’,但他可以做出很出彩的文章,是一名很有新闻敏感的记者。”郑重说。
黄裳晚年,与他交往较多的是陈子善。陈子善说,第一次见到黄裳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一则因为年轻,一则因为参加鲁迅全集书信卷的注释,书信卷里涉及的很多人都与黄裳有过交往,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找上门去了。“黄裳对我这个后辈注释鲁迅全集以及后来编周作人的集外文都很肯定。记得有一次跟黄先生谈起周作人的新诗,黄裳突然问我,‘周作人有一本《过去的生命》你看过么’,我说我听说过,但是还没看过,也还没来得及去找。黄先生突然就笑了,转身就到他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送我。这是我第一次收到黄先生的赠书。他觉得既然我编周作人的书,他的作品就应该多读。”
谢春彦画像追思
黄裳先生不仅是散文家,也是沪上有名的藏书家。陈子善记得有一段时期,他每个星期天都要去文庙旧书集市找书,只要有时间,就去黄裳家跟他汇报找到什么书。黄裳先生喜好收藏明清版本的古籍善本,像明刻本、清刻本等等,在这方面他是国内一流的。“他知道我的兴趣在新文学,所以从来不跟我谈古籍,因为明清版本我一窍不通。他每次都要问我买了什么书。我就拿两本书放在他的写字台上,他一看就说,‘你这种书都要。’我买的书自然入不了他的法眼,但是对我而言都是千辛万苦淘来的。”
“黄先生待人接物有自己的原则、想法,你不能强迫他做什么事,但是他高兴就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陈子善说,“很多人在回忆录里都谈到黄裳先生不善于言谈,尤其你谈的话题他兴趣不大的时候,他就对你笑笑,这个笑的含义很丰富,你可以继续谈,他可以听,但是他不发表意见。如果你突然谈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他就又会接话茬滔滔不绝地谈下去。”
在追思会上,画家谢春彦带来了一幅小型的黄裳肖像画。为了在追思会上展示这幅为纪念黄裳而作的肖像画,谢春彦在凌晨4点就起床赶工,并在肖像画上赋诗一首,记叙与黄裳先生交往的点滴过往。谢春彦说,黄裳先生很沉默,话很少,而他以前最怕触碰到黄裳先生的眼睛,觉得黄裳先生的眼睛中透露着几分智慧,几分狡黠,他想用这幅肖像画试图传递黄裳先生眼睛的神韵。
《黄裳文集》的编辑刘绪源说,黄裳先生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与黄裳先生的文体有关。黄裳是完整保留鲁迅、周作人这一派文体味道的作家。
复旦大学出版社学术总监陈麦青回忆起黄裳先生对碑帖文章的关注,媒体人陆灏、顾村言、张明扬等还就与黄裳先生的交往及其文化意义谈了各自的体会。旁听追思会的部分读者也参加了交流与研讨,参加追思会的读者还获赠印有黄裳先生印鉴的《爱黄裳》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