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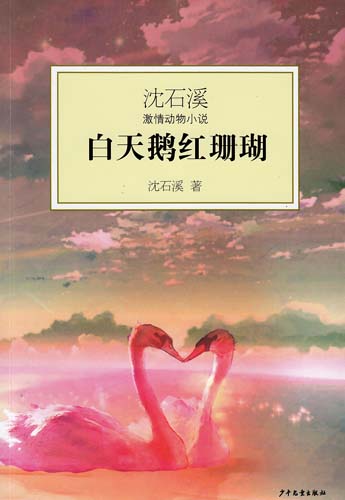 沈石溪的短篇动物小说只要一开场,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故事氛围迅速把我们环绕起来。他的开门见山的叙述往往一刀挑开情节的锁链,从这起始的一环开始,故事角色的行动便再无止歇地一路向前。沈石溪的动物故事讲究叙事铺展的紧凑,他的叙述很少在一个固定的场景处停顿逗留;而当他开始在某一个叙述点上放缓脚步时,则意味着他要把一个令人激动的故事高潮推到读者面前了。不错,沈石溪的小说永远不会缺乏高潮,而那个高潮,一定被赋予了某种非同寻常的震撼力。比如《灾之犬》中被“我”多次丢弃、伤害的“花鹰”在“我”危急时刻的突然现身,《老马威尼》中满怀恐惧的威尼为挽救马帮毅然走向虎口的场景,《烈鸟》中的红脸鹩哥王终于开腔放出鸣唱的那一刻,以及《羊奶奶和豹孤儿》中母羊将养子花豹顶入悬崖,自己也随即跳崖的情景。我们在抵达这些情节高处的时候,会感到自己的血气仿佛也随之隐隐沸腾起来。 沈石溪的短篇动物小说只要一开场,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故事氛围迅速把我们环绕起来。他的开门见山的叙述往往一刀挑开情节的锁链,从这起始的一环开始,故事角色的行动便再无止歇地一路向前。沈石溪的动物故事讲究叙事铺展的紧凑,他的叙述很少在一个固定的场景处停顿逗留;而当他开始在某一个叙述点上放缓脚步时,则意味着他要把一个令人激动的故事高潮推到读者面前了。不错,沈石溪的小说永远不会缺乏高潮,而那个高潮,一定被赋予了某种非同寻常的震撼力。比如《灾之犬》中被“我”多次丢弃、伤害的“花鹰”在“我”危急时刻的突然现身,《老马威尼》中满怀恐惧的威尼为挽救马帮毅然走向虎口的场景,《烈鸟》中的红脸鹩哥王终于开腔放出鸣唱的那一刻,以及《羊奶奶和豹孤儿》中母羊将养子花豹顶入悬崖,自己也随即跳崖的情景。我们在抵达这些情节高处的时候,会感到自己的血气仿佛也随之隐隐沸腾起来。
沈石溪是一位说故事的好手。他懂得如何在自然流畅的叙述中将读者一步步逗引到故事情节的深处,知道怎样的一个转折、一句说笑,会给故事增添比文字空间多得多的趣味。在《灾之犬》中,他先写灾犬“花鹰”带给猎人艾香宰的种种祸事以及巫师为“花鹰”所下的不祥断言,从而使“花鹰”成为了一头不受欢迎的猎犬;继而一个转折,安排身为“知识青年”的“我”撇开迷信,将无人问津的“花鹰”收为已有。但随着“我”所遭遇的种种“不幸”迹象的显现,关于“花鹰”的谶言愈来愈占据了“我”的脑海,最终促使我为了摆脱它而无所不用其极。而就在“我”终于迫使“花鹰”离开自己之后,它却不计前嫌地从印度鳄的口边舍身救下了“我”。故事最后,还是一个转折:我重新搭起狗棚,准备迎接“我”的“花鹰”,并且决定“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让它离开我了”;然而这一次,“花鹰”能否脱离鳄口,重新回到“我”的身边,则变成了一个永远的悬念。小说层层的起伏与转折,将读者的注意力完全系在了那支射出去的故事之箭上。
在沈石溪的动物小说里,总出没着那么一位作为叙述人同时也作为故事参与者的“我”。这个“我”有着属于人的普通的贪婪、自私与俗气。他出于捡便宜的心思要来了猎犬“花鹰”,又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它甩掉;他为着笼里沉默的鹩哥想方设法,只是为了拿它换个好价钱;他在确认自己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放下了指向断腿母豹的枪头,因为“子弹会损伤美丽的豹皮”。这是一个多么不掩饰自己的自私的普通人!故事里的他甚至因为这份坦率的自嘲而变得有些可爱起来。同时,他的俗气也不时反衬出动物身上的义气与骨气。而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份贪小自私的气味在猎犬“花鹰”不记旧恨前来救助“我”时,在红脸鹩歌王歌尽泣血而亡时,在母羊灰额头与豹孤儿先后坠落悬崖时,早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默的敬畏。
沈石溪的许多动物小说都以客观的故事场景收结。这样的收尾使得我们在故事情感最为激荡的结局处,却几乎体察不到叙述人的情感温度。这份来自叙述者的沉静与故事结局所包含着的强烈的情感冲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在“收”与“放”之间所形成的充满张力的叙述语势中,蕴蓄起一股有如将爆发的火山般的情感力度。这份情感窜行在表面冷峻的文字之下,仿佛随时都会喷薄而出,却又恒久地保持着这样一种即将喷薄的姿态。
这也是一种最有力量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