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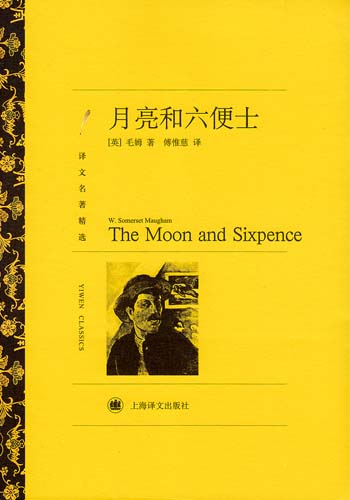 有人说过,如果小说里没有爱情,那么这种文体将失去所有的女性读者。 有人说过,如果小说里没有爱情,那么这种文体将失去所有的女性读者。
在某种条件下它是成立的。不过,这句话毋宁说成,如果小说里没有爱情,它很难把想要表达的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小说需要爱情,并不在于它要招揽女性读者。
就拿这部《月亮和六便士》而言,它欲图描写一个不食人间烟火、摒弃一切世俗感情与道德责任的男性艺术家,也不得不借助他对爱情的态度做标尺,在文中,他同三位女性的关系成为主要内容跟重要线索。
书中在描写斯特里克兰德跟女人的关系时,不乏连珠妙语,让人忍俊不禁。尽管我几天前负气似地在微博上写出些调侃这类男人的话,但那并不能代表我的本意。实际上,我从没像现在这样,给予男人以如此大的宽容度跟理解。这些进步都源自于本书。
斯特里克兰德是个男人中的特例,他被上帝选中,要担当描摹人类力量与灵魂的艺术家,这是一件苦差,要弃绝尘世的舒适享受、文明社会的道德伦理法则、以及对肉欲情感的追求,这是一桩需以纯精神的力量为之的工作。于是他抛妻弃子,逼死情人,跟南太平洋海岛上的土著少女姘居,渡过十几年穷困潦倒的生活,最后死于麻风病。在常人看来,他是一个心智不健全、缺乏道德责任感的恶棍,但是这种舆论的审判跟他心中想要冲破人性枷锁的力量比较而言,实在微不足道。他的使命感,抑或是自己也无法操控的灵魂深处的创作欲望让他在痛苦中本能地追寻着。
这是一个不凡的男人,但他一定得是个男人。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不同。斯特里克兰德说,女人都没有大脑,正像很多女人说过,男人都用下半身思考。这些偏执的看法多少能反映出这类不同。女人视感情为生命的全部,而这在男人的生活中只是一部分。对于这个道理,无论是在张爱玲还是毛姆的笔下,都是殊途同归的。毛姆写的是男人在女人逼迫之下的疲惫,张爱玲则代表女人在男人负心后的宽恕。
斯特里克兰德夫人,她跟斯特里克兰德初见于华年,也曾有过如梦似幻的爱情,她有爱艺术的热情,却没有相应的创造力跟鉴赏力,她对艺术的追求主要表现在宴请名作家吃饭,却从未察觉相伴十七年的枕边人恰是一个举世罕有的艺术天才。她对艺术的爱是一种叶公好龙,当因为艺术而导致的重大牺牲骤然来临,她被这种摧毁力冲击,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憎恨。这样一个表面热爱艺术的女人,处在世俗的中心,恰恰是最现实的。她不会像勃朗什那样寻短见,当丈夫为了学画不惜离家出走,她并没有沉湎在悲伤之中,而是马上面对现实,偃旗息鼓自谋生路,甚至为自己的生存,去编造丈夫与情人私奔的谣言。对于这样一个人物,作为叙述者的“我”从一开始的喜欢同情,到后来不禁也有些菲薄,但以我看来,她的做法是颇值得借鉴的,既然遇见了不可挽回的男人,又要避免自己受伤,那么现实到庸俗的做法是最佳的方式。如果不被丈夫抛弃,她会像个幸福的主妇,守着哪怕肤浅的艺术情操,活得华丽光鲜。最终她在小说中的形象堕入庸俗,但成为一部近乎完美的弃妇生存法则。
我原本以为自己会最喜欢斯特里克兰德的情人勃朗什,结果她却成为我最看轻的一个。她至情至性,又无法无视自我的存在,可以代表绝大部分女人的心态。她成了斯特里克兰德的牺牲品,在他的灵魂企图挣扎出肉体的努力失败后,在他精疲力竭的时候,充当了一剂良药。她就像一个被寄生体,任他附着于上,孕育出艺术的珍品,在供给光自己的养分之后,萎谢如蝉蜕。可怜的勃朗什,也许她本是茨威格笔下的痴情女子,但在斯特里克兰德的绝情之下,她是连半分同情和尊重都得不到的,最终只能无奈地死于凄凉,门外站着爱她的男人,她却连见一眼的仁慈都没有。应了那句多情总被无情恼,我想起云板里的悦离,都是面对无情的男人欲图一搏,却又输给他,输得一败涂地,且一点也不值得世人挂念。
斯特里克兰德一直在等待埃塔这种女人,任何一个有所成就的男人都要遇见一个可以成就他的女人,这似乎是上帝给这台极品机器配备的一个专用的电源适配器,她是原生态女人,未受分毫现代文明的沾染,对艺术家有种出于本能的崇拜,可以做到毫无自我,无私奉献,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对画家的爱情矢志不渝,即便是他患了麻风,也不离不弃。
在作者对画家的描写中,总不忘提及他那野性的外表、充满肉欲的唇,画家终身都试图摆脱平凡肉身之中的情欲带给自己的羞耻感,他总是试图扯断高尚的精神理想跟肉体需求之间的关系,以为这就是触摸艺术真谛的不二法门。其实,他的艺术升华恰恰发生于发泄肉欲后的脱胎换骨的轻灵感之中,所以他需要的是给他自由又肯满足他情欲的女人,这世上一定有女人是甘于做埃塔的,但这种纯然的自我牺牲并非吾辈所能达成,人总该有点自己存在的意义,所以她也没什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