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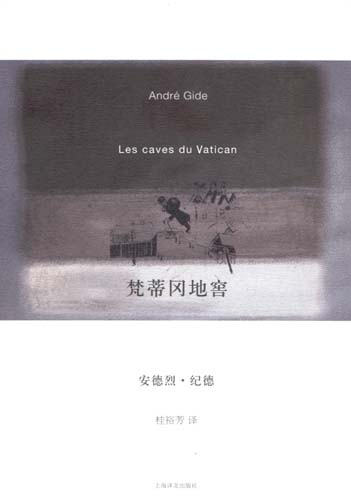 80岁的桂裕芳教授,有着那一代人特有的谦逊内敛。作为北京大学法语系资深教授、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桂裕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只是一名教员,对纪德的研究不多,深恐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深度。 80岁的桂裕芳教授,有着那一代人特有的谦逊内敛。作为北京大学法语系资深教授、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桂裕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只是一名教员,对纪德的研究不多,深恐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深度。
可是,真正与记者谈起纪德,桂裕芳教授却娓娓道来,脉络清晰。30年前,她就因为自己的喜爱,翻译了纪德的名篇《窄门》;后来又应出版社之邀,翻译了《梵蒂冈地窖》。如今,这两部译稿均被收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纪德系列”,重新出版。
纪德在中国曾是空白
桂裕芳说,纪德在中国从未真正的“热”过,他甚至不如视他为精神导师的萨特、加缪等人在中国的影响。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内对他的介绍就不多,原因很复杂。纪德是一位非常关心社会、时事的作家,他反对法国殖民主义,对国内的局势不满,因此一度非常向往苏联。刚好,苏联邀请纪德去访问。回来之后,纪德写了一篇《访苏联归来》,指出了苏联的一些毛病,比如着装千篇一律之类的现象,并未完全否定那个制度,却因此被认定为“反苏”。北大的盛澄华教授,是一位对纪德有非常深入研究的学者。“文革”期间,“纪德的崇拜者”却变成批判他的罪状之一。另外,纪德是一个同性恋者,这也是我们在几十年前容忍不了的。
上世纪80年代之后,纪德的作品常见收于一些外国文学的小说集,很少单独出版。直到2002年前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才联袂推出了《纪德文集》。今年,上海译文再次出版纪德的作品。桂裕芳说,时代的变迁,终于让一位伟大的作家,逐渐得到公平对待。
纪德的反叛与讽刺
桂裕芳第一次接触纪德的作品是《田园交响曲》。《田园交响曲》讲述牧师收养了一位盲女,用音乐、歌唱向她进行文化启蒙。女孩非常幸福,并爱上了牧师。女孩成年之后,终于把眼睛治好。可是,重见光明之后,女孩却投河自杀了。因为,女孩在心里对牧师已经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想象,并爱上了那个形象。这个形象不是牧师,而是老人的儿子。书中“那种人性的期望与现实无法调和的幻灭感”,让桂裕芳阅后极为震撼。
1980年前后,桂裕芳就译出了纪德的《窄门》,《窄门》是她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窄门》中的感情矛盾而又真诚,女主角既想忠于宗教,又想弥补母亲对父亲不忠的罪,因此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带有一种清教徒的残酷性。纪德正是借此,表达对清教徒压制人性的批判。
虽然离翻译《窄门》已经过去30年,桂裕芳仍清晰记得书中两个爱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一个人在门里,一个人在门外,痛苦而又坚决地分开。桂裕芳说,纪德的文字并不华丽,但十分流畅,是一种顺着感情的宣泄,译起来非常舒服。
纪德身后的法国50年
纪德的思想中,最主要是“自由”。纪德之前,19世纪末,法国盛行的是象征主义,无所谓真实与虚幻,甚至走到极端变成“达达主义”,这虽然也是一种自由,却不是纪德想要的,他向往的是不违背现实的自由。
纪德赞成东西要先有感觉再写出来,觉得象征主义的东西有些“造作”。他认为,海滩的沙粒如何柔软,如果没有亲自用脚踩一下的话,你是写不出来那种感觉的。
桂裕芳认为,纪德最伟大的地方,是他从20世纪一开始,就与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创办了《新法兰西评论》,这份刊物的影响非常大,各种不同流派都可以参与讨论、批判、歌颂,《新法兰西评论》为法国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辩论场所,对法国的文艺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年,如果一部新作品能够在《新法兰西评论》上获得肯定,作品肯定会好卖的不得了。
1951年,纪德去世时,法国作家墨里亚克曾说过一段话,大致意思是:一旦盖上纪德的墓石,就把法国50年的精神生活盖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