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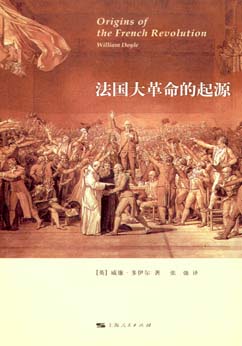 尽管已经过去200年,法国大革命至今仍吸引着无数后人的想象。因为它是一切现代政治革命的原型,其孕育的现代政治思想也决定和形塑了迄今为止的世界,简言之,脱离法国大革命是不可能理解近现代世界历史的。然而吊诡的一点是: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现象,人们却迟迟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它究竟是怎样爆发的。 尽管已经过去200年,法国大革命至今仍吸引着无数后人的想象。因为它是一切现代政治革命的原型,其孕育的现代政治思想也决定和形塑了迄今为止的世界,简言之,脱离法国大革命是不可能理解近现代世界历史的。然而吊诡的一点是: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现象,人们却迟迟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它究竟是怎样爆发的。
与通常的设想相反,革命之所以在法国爆发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虽然当时法国不可避免存在着一些社会不公和压迫,但与其他邻国相比起来却不算最难以忍受的,甚至与法国较早的历史相比起来还算是好的。传统的解释常常强调资产阶级在革命爆发中所起的作用,但更深入的研究却进一步表明:当时资产阶级不但人数很少(仅占全国人口6%),对政治事务总体而言都不大感兴趣,而且在当时这个流动性很强的社会里,资产阶级和贵族并非两个泾渭分明的群体。似乎越是深入研究下去,越是发现关于法国大革命如何爆发的许多假设和解释都难以成立。
这可能也是难免的。大凡这类极其重大的历史现象,总是在各种因素高度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下产生。这些因素本身大多早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而其相互作用的机制更是难以捉摸,因此不要说后人,即使是亲历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也常常有着无法看清事态起源和走向的困惑。用托克维尔的话说:“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而变得不可理解了。”因此威廉·多伊尔首先另辟一部分来讨论历来解释这一难题的三个历史流派,分析他们的观点之可取和不足的地方。
随后的章节分为两大部分:“旧制度的瓦解”和“权力之争”。这一安排体现了作者的总体观点,即法国大革命(其实所有的政治革命都是)首先是旧制度危机的结果,用社会学家斯考切波不无夸张的话来说,革命常常是国家崩溃的结果而非原因,革命者只不过是把它“顺手从大街上捡起来”罢了。与之相辅相成的现象则是社会和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也许可以说:旧制度的瓦解使革命的到来不可避免,而政治斗争则决定了革命何时以什么方式到来。
法国这个看似强大的欧洲大国在1789年竟会走向国家瓦解,确实是当时许多人都大惑不解的。作者从五个方面入手讨论了旧制度的这一失败:财政危机、政府体系的问题、反对者、公共舆论、改革的失败。所有类似革命中的国家瓦解,基本上都能看到这五个问题熟悉的身影。无论法国、俄国还是中国革命,政府首先都深陷于一个无法自拔的财政危机的泥潭之中,而且往往在此刻仅仅通过财政手段是无法治理财政问题的。而当时的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弊端使得体系的每一层面充斥着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和效率低下,最终即使有政治家看到了危险迫在眉睫,却仍然无法推动这个庞大的体系转向改革以挽救自身。如书中所言,“阻挠国家改革的不是那些反对的力量,而是政府本身的惰性、不可靠和优柔寡断”,甚至旧王朝的瓦解和覆灭,也不是因为反对派或革命者,而是因为其自身内部结构型的矛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改革,改革者的选择往往极少。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一些改革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结果却反而使人们对剩下的束缚更加难以忍受了。托克维尔曾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历史上很多国家的改革不但没有恢复政府的制度化权力,反倒加速了国家的解体。此外,改革通常意味着要将一些未曾尝试过的观念付诸实践,后果却难以确定,很可能反倒伤害了本已危难脆弱的局势。这就是为什么改革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因,即使是失败的改革者,我们也应对他们的历史困境予以同情之理解。
虽然可能“改革摧毁了改革派政府”,但改革一旦失败,旧制度的命运也差不多确定了,因为一个无力进行自我改革的政府,革命的暴风雨到来就已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不同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被卷入到这个风暴眼中来:贵族、官僚、教士、军队、资产阶级、市民、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预谋要搞一次革命,不同阶层的心理也不一样,他们中较为共同的一点也许是希望法国有所改变,然而这所有力量放到一起的冲突结果,却造成了一个所有人都未预见到的大革命。在这地狱之火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酝酿了大革命的公共自由的观念和喜好是最先消失的,这是我们尤其值得记取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