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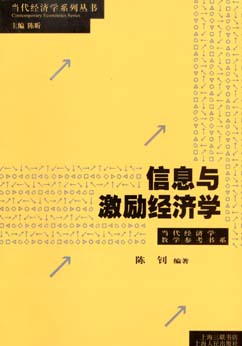 记得自己还是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曾和陆铭(当时我们是同班同学)合作过一篇用效率工资模型解释国有企业为何效率低下的文章,后来该文发表在1998年的《经济研究》上。现在想起来,这应该算得上是我早期应用信息经济学的记录了吧。不过,直到2002年,我才开始参与信息经济学方面的教学。那年秋季,我加入了由张军老师负责的研究生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后来其中的“信息经济学”部分就成为我负责的内容之一。那些讲稿不久编入了张老师主编的《高级微观经济学》教材,记得当时主要参照的是Mascolell等人的以及Varian的高级教程中的相关内容。从2003年起,我又与经济学院的陆铭博士与寇宗来博士共同开设《激励理论》,用的是Laffont和Martimort的教材《激励理论(第一卷):委托-代理模型》。 记得自己还是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曾和陆铭(当时我们是同班同学)合作过一篇用效率工资模型解释国有企业为何效率低下的文章,后来该文发表在1998年的《经济研究》上。现在想起来,这应该算得上是我早期应用信息经济学的记录了吧。不过,直到2002年,我才开始参与信息经济学方面的教学。那年秋季,我加入了由张军老师负责的研究生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后来其中的“信息经济学”部分就成为我负责的内容之一。那些讲稿不久编入了张老师主编的《高级微观经济学》教材,记得当时主要参照的是Mascolell等人的以及Varian的高级教程中的相关内容。从2003年起,我又与经济学院的陆铭博士与寇宗来博士共同开设《激励理论》,用的是Laffont和Martimort的教材《激励理论(第一卷):委托-代理模型》。
在这几年间,我发现经济学科招收的硕士研究生数量在惊人地增长,然而,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会最终为做学问而攻读博士学位,我们也常常不得不面临众口难调的困惑,要么有些学生“吃不饱”,要么更多的学生“消化不良”。记得当时我们西方经济学学科组曾经提出过将硕士生分成两个班开课的设想,而读者手中的这本《信息经济学》便是我所酝酿的面向大多数硕士生(包括本科生)的教材:遵循主流经济学的规范而不是信口开河,强调经济学的直觉而不要求掌握复杂的技术,引导读者观察与思考现象而不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
2004年初,经济学院主管教学的李洁明副院长找我为基地班的本科生开设《信息经济学》课程。当时,本书大约才完成四至五章的内容,教学进度的安排促使我加快了写作,等到学期结束时,大部分的初稿也基本完成了。算下来,从2002年动笔到2004年9月份交稿给出版社,前后差不多刚刚好花了两年时间。现在回想起来,之所以如此费时也是因为自己希望本书尽可能的“完美”,所以我常常就某些内容找好几本程度不同的教材加以比较,有时也从论文中体会精髓,力求在简化的基础上再加以简化但又不使内容有所“缩水”,也力求在简化的同时保证逻辑上的严密。这样的确占用了不少时间也难免影响其它工作,但这又何尝不是有意义的工作呢。
在写作期间,我也曾将本书的部分章节放到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的网站上供同学们下载。意想不到的是,此后陆续有一些高校的教师向我索取全部的书稿,希望拿它做《信息经济学》的教材用书。在他们那里,我再次感到中国的经济学教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目前已经有大量的经济学教材或被翻译、或被编写,然而,从教学的实践来看,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本土化”的工作,需要把中国改革以来大量丰富的素材融入到经济学分析之内。我想,这也是我编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吧。也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我在本书最后加入了“转型的信息与激励经济学”这一章内容,从信息与激励的角度结合实际中国的情况对转型问题加以初步的讨论。
交稿后不久,我来到牛津大学访问。我发现,牛津经济系所开设的部分课程内容与本书直接相关,如Meyer博士的《谈判与合同》、《激励、信息与组织》、Klemperer教授的《拍卖理论》,尤其令我感慨的是,这些课程都有大量出色的习题给学生很好训练与启发。我想,结合今后的教学,我会在适当时候为本书补充更多的习题。
事实上,本书也凝聚了很多人的工作。经济学院的三位研究生曹诗画、蒋星与刘君同学最早阅读了本书的部分初稿,他们的意见与建议使本书内容更为易读。陆铭博士不仅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而且还替我收集了书中部分的“阅读素材”。我也时常利用各种机会就本书的某些概念或内容向他人求教印证,听取他人对本书的意见与建议,在此,特别向中山大学的王则柯教授、剑桥大学的林暾博士、复旦大学的陆铭副教授、王永钦博士、寇宗来博士表示感谢。最后,我也要感谢家人对我的支持与理解,感谢我的妻子在生活上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即使是我在英国期间也不例外。当然,我也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对本书出版工作的支持,特别是李娜编辑为本书所付出的努力。
陈钊
2005年春于牛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