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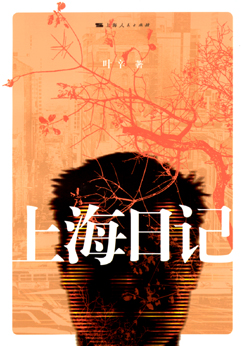 移民潮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社会现象,八十年代,人们谈得最多的是出国移民,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由边缘地区向大城市移民的趋势越来越烈,《上海日记》写的就是这么一群新上海人。 移民潮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社会现象,八十年代,人们谈得最多的是出国移民,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由边缘地区向大城市移民的趋势越来越烈,《上海日记》写的就是这么一群新上海人。
《上海日记》是著名作家叶辛最新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写了一位从贵州来的大学生全小良在上海求职求生存的心路历程和坎堪命运。这位从《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等作品一路走来知青作家,秉承他关注社会,关注低层老佰姓的创作视角,敏锐地捕捉到了新上海人这样一类特殊人群在上海这样一个城市里的奋斗历程。
可以想象,人类试图改变自己和家族命运的奋斗总是悲壮的,总是带着血泪,带着挣扎的,无论是《外省人》,还是《人生》,严酷的现实对主人公的品德、意志、有着更为严酷的拷验,显然,《上海日记》里的全小良没有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如果说他刚进报社工作时还存留着学生时代的正义感,并且凭着这些正义感拒绝了十万元人民币的诱惑,将一个严重的房产质量事故公示于众,从而引起了他人生一系列的改变。而当他陷入失业的绝境时,他对人性的错误判断,及某种媚钱媚色,渴望借助爱情一步登天的侥幸心理,便使他的人生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失败,从而令其人物本身也具备了悲剧色彩,这样的全小良如果不能迅速在心理上、思想上修练并成长,如果不能真正的在心理上自爱自立,他就不可能逃脱悲剧的命运。
全小良在爱情上的实用主义也是投机的,不严肃的,他和苗杉真心相爱,但却从未为她付出过什么,完全的拿来主义。他不爱苏悦,却又禁不起苏悦身体的诱惑。他明明知道自己和乔海贝不是一路人,却还痴人做梦地妄想有朝一日能成为身价数亿的乔海贝的丈夫,他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个人性格的悲剧。他是这个城市的新移民,他居无定所,而在他的心理上,也缺少一种心的归宿,缺少内在文化的定力,缺少自己成熟的价值观,这是他成为悲剧人物的根源。全小良在上海奋斗的遭遇,仅仅只是拉开了一层序幕,更严酷更惨烈的搏杀才刚刚开始,一个没有文化定力的人是可悲的,一个没有文化定力的民族就象没有根的浮萍会随波逐流,是危险的,值得引起我们的文学家、社会学家的倾心关注,好在我们有了《上海日记》这样的文学作品,有了近几年持续不降的以南怀瑾为代表的国学图书的热销为我们日渐沙漠化的文化下了一场春雨,一个文化的春天必将到来。我们试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