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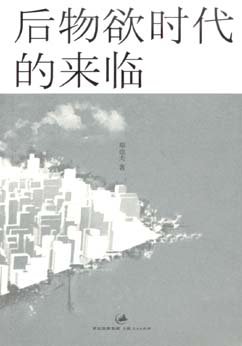 “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的这句名言,一般被理解为宽容异己的原则。但与之相关的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是,如果大家都自觉地放弃说话,还需要捍卫什么权利呢? “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的这句名言,一般被理解为宽容异己的原则。但与之相关的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是,如果大家都自觉地放弃说话,还需要捍卫什么权利呢?
不说话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说话本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它不是面包被窝,不是刀枪剑戟,不是任何一种权力,可以凭借来推翻或改变什么。权力是积极的,而说话只是一种权利,权利是消极的,捍卫起来千难万难,运用起来于事无补,放弃起来则易如反掌。于是不说也罢。
对于这点,郑也夫有更深切的理解。这个自称好斗的超龄愤青,写的东西火气也大。《抵抗通吃》打开来,满纸火药味,从高考政策到长假制度,从轿车养护费到节水措施,没有他论不到、批不着的。偏偏这样一本愤世嫉俗的杂文集,开篇第一回却是“我能影响中国吗”,这就深有意趣了。
郑也夫自陈是“中国最早提出反对发展私家车的人”,但喋喋不休后,街上跑的私家车还是变多了。他批西直门地铁的链接糟糕,浪费纳税人的钱,还侵犯了公众知情权,道理说得滴水不漏,批评也到位,但地铁难不成会改建?似乎郑也夫不能影响中国,似乎谁也不能凭几句话影响中国。冒出一个不识相的怒目圆睁者,反而给人奚落修养不到家,也让更多的人们疑惑甚而愤怒:你既然不能直接改变我的境遇,何苦多费口舌徒增我的烦恼?可恶!可怜郑也夫,落了个哪一头都不讨好。
但是郑也夫却认为,不合作、不妥协,保持批评的姿势,维护说话的权利,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是另一种权力。一两个人说话没有用,但说话的人多了,力量就不可小视了。在底层的大多数即使什么权力也没有,至少可以运用自己说话的权利,心里生质疑,发之为声。声音积攒得多了,分贝高了,便振聋发聩、能裂金石。
如此看来,能提醒大家都来发声,或者干脆跳起来大声说话,以作表率的,可谓意义非凡。就像郑也夫自己说的,“有人可能打不过人家,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就是这种人。有人看我绝对傻B,都像你们那样聪明,就完了。”既已知说话的无用,还能在失望中持续地、执拗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实在是悲剧性的壮烈。
偶尔想去法庭旁听,大清早带着身份证赶在法院门口,却被告知旁听证发完了。如果所有的人听到解释便乖乖地掉头,如此碰壁两三回后,便打消旁听的念头,某种形同虚设的旁听制度便可以一直执行下去。郑也夫这样的刺头却非要问清楚:几点开始发证?有多少旁听证?是否公示?这样问的人多了,即使为应付质疑和提问,制度也要修正和完善。
全国高考,一样地命题、一样地判卷,各省的录取分数线能相差100分,招生也有不同的配额限制。郑也夫在报上反复地“挑衅”和“抗议”,也有学生将教育部告上法庭,即使郑也夫的声音微弱至于“无用”,即使法院不受理此案,如此前赴后继,高考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就孕育其中了。
无论说什么,说话本身就很重要。没有阻力,有权势者可以轻而易举囊括权力、财富、地位、名分,一个都不少——即为通吃。说话、抱怨、质疑、发问,是防止他们通吃的第一道阻力。明了这层因果,看看郑也夫如何抗拒通吃,再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均衡、更合理、更完善、更合适多数人生存的制度才有指望。
郑也夫已经说话了,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