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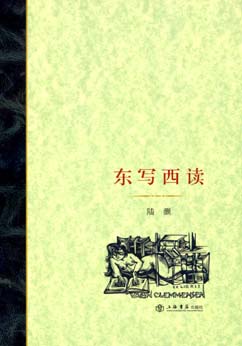 我是学历史的,有一种奇异的“考据癖”,喜欢“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现实。每次读到新一期的《万象》,总不免想二十年后不知又有多少人要写文章来回忆与“我的朋友陆灏”在一起的日子。三五十年后如果某个研究学术史的小资女生以“陆灏与《万象》派”这样的题目来作论文,那是肯定会给导师表扬为“有识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总结规律性”的。 我是学历史的,有一种奇异的“考据癖”,喜欢“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现实。每次读到新一期的《万象》,总不免想二十年后不知又有多少人要写文章来回忆与“我的朋友陆灏”在一起的日子。三五十年后如果某个研究学术史的小资女生以“陆灏与《万象》派”这样的题目来作论文,那是肯定会给导师表扬为“有识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总结规律性”的。
然而,陆灏放手《万象》才不过一年,报纸上却连篇累牍地谈起“陆灏家的客厅”来。细究之下,才发现原来“‘美妇人’终于生了第一个孩子,名为《东写西读》”(李怀宇语)。
在《东写西读》的封底,陆灏写了一段表白性质的话,先是借钱锺书先生之口引了一句梅里美的名言“我只爱历史里的掌故”,接着说:“这种追求小趣味、看不到大问题的读书方式,虽然在正宗的历史学家看来,只是文人们地地道道的浅见薄识,但对我这样读书只求趣味不为写论文的人来说,几乎就是全部的兴趣所在。”
这样的读书趣味,说一句托大的话:深得我心。当然,以我一惯的怪癖,令我感到兴趣的,除了“历史里的掌故”之外,更多的还是大家与“我的朋友陆灏”的故事。
记得毛尖在一篇文章里说,到上海,说晚上与陆灏有约,那说明你既有面子又有格调。这些跟陆灏有约的人里,阿城可算一个。阿城是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好像是他的《孩子王》《棋王》大红大紫的时候吧,有个女记者采访他,惊讶于他的无所不会,最后问了个傻问题:“你还有什么不会的?”阿城认真想了想,说:“生孩子。”阿城到上海来,对着陆灏大侃书法。他不谈二王,不谈颜柳,也不谈苏黄米蔡,而是给他上了一堂基础课——如何执笔!阿城说,古人写字时,笔杆是左右转动的。陆灏不信,当场拿了根筷子做试验,结果发现转了就不能写,要写就不能转。阿城开导他,你要是转成了,你就是王羲之了。陆灏仍然不信,翻书,发现清代的刘墉还真是这么写字的,甚至有因为转得太厉害致使笔都掉地下去的时候。
叶秀山也曾讲过一段关于书法的掌故。叶秀山是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哲学家,但他不仅对哲学很在行,对京剧、书法等传统的老玩艺都很在行。叶小的时候,父亲告诫他,学字不要学赵体,当时还不甚明白,到“文革”中,看到哲学所副所长陈冷一写检讨自我批判,供述自己的“罪状”之一是小时候偷懒没有临习难度较大的欧体、柳体,而贪图容易临了赵体,造成以后写字没骨架,软绵绵的没有朝气,这才明白父亲的深意。练书法练成了罪状,希望只是那个疯狂年代里的事。
比起外来的,出入陆家“客厅”的本地文化人当然更多。当然,如果是老上海的耆旧,那座上客就变成陆灏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留下来的文化名人中,施蛰存算一个。“午后的阳光撒在窗外的阳台上,窗下书桌上零乱地堆着书报文稿信札,九十岁的施蛰存老先生坐在书桌前,嘴里衔着雪茄。我坐在他身旁,抽着烟,一老一少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这个场景,多像是简·奥斯汀笔下的英国乡村,又多么像是王家卫电影里的老上海!坐在施蛰存的书桌前,听他谈《石秀之恋》,谈完了,还能从老先生的书架上“顺”走几本原版的或绝版的、扉页上贴着“施蛰存无相庵藏书之券(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的好书(老先生散书)。这种好事,是个读书人就很羡慕吧,可人家呢,“当时只道是寻常”。
这份名单要继续开下去,还有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钱仲联,董桥,林行止……毕竟,陆灏的“客厅”里招待过上海的大半个文化圈呢。在这本《东写西读》里,提到的还只是极少数。提到他们,陆灏也并非是存心夸耀,只不过是自然地想到哪写到哪,可是在我们,却情不自禁地要艳羡他那份得天独厚了。可陆灏呢,正如钱锺书先生在给他的信中所说:“具有如此文才,却不自己写作,而为人作嫁衣,只忙于编辑,索稿校稿,大似美妇人不自己生男育女,而充当接生婆。”
还好,接生婆下岗后,生了《东写西读》这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