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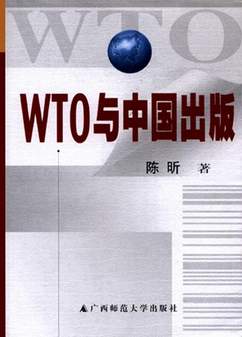 编者按:2001年11月10日,卡塔尔首都多哈喜来登酒店会议厅,WTO成员国的部长们正在为中国入世进行着“九十九度加一度”的表决。自此,中国终于跨入WTO的门槛,成为这一多边经济组织中的一员。中国经济生活与WTO规则的讨论便由虚拟变成了现实。入世之后,中国书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采访了率队来京考察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社长陈昕同志。陈昕同志对书业的全球化命题有深入的研究,出版过《WTO与中国出版》的专著。他的思考与分析富有理性与建设性,对书业界有一定启发。 编者按:2001年11月10日,卡塔尔首都多哈喜来登酒店会议厅,WTO成员国的部长们正在为中国入世进行着“九十九度加一度”的表决。自此,中国终于跨入WTO的门槛,成为这一多边经济组织中的一员。中国经济生活与WTO规则的讨论便由虚拟变成了现实。入世之后,中国书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采访了率队来京考察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社长陈昕同志。陈昕同志对书业的全球化命题有深入的研究,出版过《WTO与中国出版》的专著。他的思考与分析富有理性与建设性,对书业界有一定启发。
记者:陈昕社长,多哈表决第二天,就想通过电话采访您,请您谈谈中国书业入世后的产业趋势,只因您太忙,没能在办公室里“逮”着您。没想到在北京采访到您,而且由您亲率世纪出版集团的管理高层及各社总编辑来京调研,是“入世”的扳机启动了你们的工作新节奏吗?
陈昕:这只是巧合。这次调研活动我们早就计划好了,北京考察完了还要去辽宁出版集团。大家都知道,10天前的多哈会议只是一个“划句号”的仪式,这之前,“冒号”已经划了15年了。这中间有几个惊叹号与中国书业有关,譬如1995年2月“中美关于知识产权及市场准入协定”。当然对中国入世具有关键作用的节点是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以及2000年5月19日中国与欧盟就中国入世达成协议。我就是受这两次利好成果的触发写了《WTO与中国出版》的小册子,就中国出版业如何应对WTO的挑战谈了我的一些思考。其中还包括我的几份出国考察报告,一份是关于日本出版流通体系的,一份是关于欧洲出版集团的,一份是关于美国出版集团的,这都应归于出版全球化的大主题,加入WTO也是这一大主题下的子命题。由于我受命组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而集团这一出版组织形式恰恰是我们加入WTO之后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应对措施,因此,书中还有一条线是对新的出版组织的培育及组建出版集团的系统思考。
记者:《WTO与中国出版》这本书大部分的内容都曾刊发在本报上,许多书业界的朋友都认真读过,请问您最近有哪些新的思考?
陈昕:多哈会议虽然说没有什么悬念,是一次“九十九度加一度”的仪式,但也让我静下心来细细地梳理了一番思路。回想起来,中国入世路迢迢,经历了15年,WTO这扇门一寸一寸对我们开启,不容易,但也给我们以足够的时间站在门外研究门内的事情。可以说,中国书业在应对WTO挑战问题上思考与探索是充分的。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版、发行微观组织的重造,这方面的议论、争论和尝试从1995年就开始了,好像你们的报纸正是在那一年改版成《中国图书商报》的,赶上这一段产业升级的时光,先是中盘雄起的大讨论,随后是对组建出版、发行集团化出谋划策,而后是对现代物流建设、超级书店联盟形成的呼吁,还有对连锁经营模式的分析等等。大部分重要文章都发在商报上。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又顺应了国际书业发展的大趋势。入世签字之后,中国参加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归纳中国入世的意义是八个字:“开放市场”“市场经济”,其核心也就是按市场经济的国际规范来思考和行事。这一时期发生的另一变化是关于出版宏观管理组织形式变革的探索,譬如政企分开,将政府的角色和职能从“办出版”转向“管出版”,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与活力,这些为入世之后政府监管职能的突显奠定了基础。
记者:入世签约之后,书业界一些人私下里议论,喊了十几年的WTO,入世时才发现书业并未即刻或全面开放,不像农产品、纺织品、金融、保险等行业马上会有“震动”性变化,我的一位朋友买了一大堆的报刊,还在网上检索了大半天,只查到“流通领域”条款下“图书、报纸、杂志、药品、杀虫剂、农膜分销将在三年内放开”,再就是“通讯与互联网”项下“增值服务(含互联网服务)入世后沪、穗、京允许合资建企业,外资可占30%股份,一年后扩大到重庆等14城市,股份增至49%。“音像”项下:允许通过合作公司的形式发行音像视像产品”。大家觉得没什么压力了,似乎太阳还是那个太阳,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对此,不知您如何看?
|